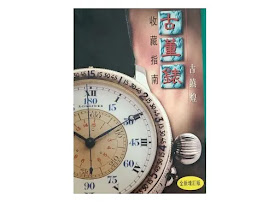今日請你細讀這首百行童話詩〈紅磚砌成的小屋〉,它的作者藍子是一九五零年代香港著名的詩人,她最喜歡的那間小屋建在幽謐的河邊。雖然她不叫朱麗葉,那個住在閣樓西窗下的少女卻像朱麗葉一樣在等待她的羅米歐;她的羅米歐不必是白馬王子,很可能是個趕鴨子的年輕人,只要他趕着兩隻鴨子來看她……。
藍子的這首〈紅磚砌成的小屋〉發表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出版的《月華詩刊》第二期。《月華詩刊》由月華詩社出版,此刊共出兩期,創刊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二開本,第一期只有八頁,第二期則增刊至十頁,〈紅磚砌成的小屋〉在僅十頁的《月華詩刊》第二期中竟佔了兩頁之多,可見十分受重视。
月華詩社最早的成員是:柏雄、草川、夕陽、波瀾、許家林、幻影和蘆荻七人,年輕的藍子剛滿二十歲,是極具詩意的少女,不知曾否加入月華詩社?
認識二十歲藍子的人恐怕不多,但,如今已八十有多的西西卻是人人都知曉的。
寫於六十多年前的〈紅磚砌成的小屋〉,不知曾否收在她的詩集内?
──2021年2月
2021年2月27日 星期六
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
寒山碧評金庸
※我看查良鏞
西城兄說,「要尊敬金庸」,我本來不想談,但網絡上已有人談及,我也不妨談談自己的看法。面書本來就是讓人們閒聊臧否人物的平台。
談到查先生,我認為必須分開前後,一個是獲鄧小平接見之前的查先生,另一個是獲鄧小平接見之後的查先生。
前一個查先生我是非常尊敬的,甚至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明報》和《明報月刊》是我重要的精神糧食。查先生獲鄧小平接見後我對他的敬佩打了折扣,特別是他風塵撲撲跑到深圳覲見許家屯,提出《雙查方案》後,我對他的尊敬大幅削減。俟後,他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博士導師之後,他的多番言行,令我對他的尊敬蕩然無存。因為後一個查先生完全否定了令我所敬佩的前一個查先生。
西城兄對查先生是近觀,或許有發現查先生未為人知的優點,我對查先生是遠望,我所望見的也是大家所望見的,故不妨公諸於眾。下文是我記述與查先生唯一見面。
--------------------------------------------------------------------------
※金庸請鐵凝吃飯我作陪
我不記得是那一天,反正是鐵凝在港短短這幾天內,我忽然接潘耀明電話,說金庸先生邀請鐵凝和我吃晚飯,我只考慮片刻便答應了。我當然知道,查良鏞老闆要宴請的是鐵凝主席不是我,只因為鐵凝是我的客人,潘耀明又得通過我去邀請鐵凝,不好意思把我甩開吧?也順便邀請了我。我與金庸雖然有點芥蒂,曾著文批評過他, 但君子坦蕩蕩,沒有甚麼是需要迴避的。
我與《明報》及查良鏞先生欠點緣份,在開辦自己文化公司之前我是一個自由投稿者,可是卻從未向《明報》投稿,而《明報》〈自由談〉卻是最多大陸仔投稿的園地。等到我自己創辦《東西方》之後卻與《明報》發生些許磨擦,前面已有述及,在此不贅。而2003年,我又寫了一篇談論金庸的小文──《譽之極至,謗必隨之──冷眼看金庸小說的爭論》,這篇小文是編者力邀下才產生的。我在文首說:「本文題目,原是三年前席間的閒談。1999年12月我在大陸參加陳序經(前嶺南大學校長、暨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副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全盤西化的提倡者)學術研討會。宴會上一位來自北京的學者端木正教授(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女兒端木美(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突然問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對北京近日關於金庸小說的爭論有何看法?我當時說:『這是沒有必要的爭論,譽之極至,謗必隨之』,並簡略談了我的觀點。原無意訴之文字,但《香江文壇》主編漢聞兄一再邀約,衹好應命。」
我在這篇小文裡說:「《金庸傳》的作者譽他為寫『寫武俠小說的『世界第一俠筆,寫社論的香江第一健筆』有沒有問題呢?絕對沒有問題……《信報》老闆林行止先生,雖然也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但兩人沒有太大矛盾。……查、林兩君只是一前一後,互相輝映,並且相信林君也無意與『查大俠』於香江論筆,爭第一。金庸小說爭論的由來,不是出於他的小說,而是出自小說之外的因素。……金庸被抬舉已久從八十年代起……溢美之聲從未間斷,有沒有問題呢?絕對沒有問題……金庸的武俠小說被吹捧為『文學革命』,金庸也被吹捧成『文學大師』……而且高踞中國現代文學第四把交椅,把茅盾等都壓下去。……甚至有人建議提名金庸參選諾貝爾文學獎。……一波又一波的吹捧抬舉,金庸已儼然成為國際級『文學大師』了……這一來令文學界頓然省悟,他們可不是鬧着玩的,是來真的的了。於是再也不敢掉以輕心,這才出現鄢烈山的《拒絕金庸》和王朔的《我看金庸》等『批金』文章,一場金庸小說爭論也由此而起。』」
至於我自己的觀點毋須贅言,只須看小標題可知。文章的小標題是:〈武俠小說終歸祇是武俠小說〉,〈金庸所獲得的尊榮是單純由武俠小說帶來的嗎?〉〈大陸的文學批評的墮落與進步〉」。武俠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有很大隨意性,無論甚麼事情都可以突然而來,毋須鋪墊,讀過文學系,遍讀世界名著的人,很難接受武俠小說是嚴肅的文學,金庸是頂級的「文學大師」這種說法。故我在最後一節說:「聖人曰:『大位不以智取』,我認為大名也不可智取,像『文學大師』之類大名如以智謀取之,往往適得其反,即使得逞於一時,往往也為日後帶來罵名。此即譽之極至,謗必隨之也!……十年後,大陸的文學界有人對金庸『文學大師』表示『拒絕』,把武俠小說從文學的神龕上搬下來,放回坊間通俗的攤檔上,顯示大陸的文學批評已有長足的進步,我感到欣然。」
2005年江蘇的電視台訪問我的朋友原南京大學副校長董健先生,就大陸把金庸的武俠小說編入中學教科書的問題問他的看法,董健不僅公開表示反對,而且還引述我跟他在閒談時說過的批評大陸過度捧承金庸的話。事後他還打長途電話給我詳述其事,談了將近一個小時。董健與我同齡,是中國極少數敢言的知識份子之一,我們有不少共同的觀點。
我上述言行,相信金庸是清楚的,金庸想宴請鐵凝順便請了我,可能是他的大度,我的應邀自然不是為了吃一餐,而是顯示我的坦蕩。我不記得晚宴是在那間酒樓,只記得我得我到酒店去接鐵凝,聯袂赴約。進入席間才知道晚宴只有查先生、查夫人、潘耀明、鐵凝和我。席間的談話內容我已不記得了,只記得大家都盡量避開談小說和武俠小說,我是盡量低調,不亢不卑,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見查先生。鐵凝離港前雖然她的秘書跟我交換電話和電郵地址,但她返京後我再也沒有跟她聯繫,所以我跟鐵凝不能算朋友,只是工作關係。
(寒山碧臉書2021年2月19日)
讀者回應:
Sk Cheung:
竊以為對金庸不必苛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雙查方案作為一家之言,後來成為不少草委的共識,對其中是非也無需較真。整個《基本法》就是一道緊箍咒,港人就算是孫悟空再生也無法逃脫。現在的《國安法》更加直截了當!再者,金庸應張浚生之邀出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並擔任博士生導師,其間發表媒體應像解放軍那樣聽黨指揮的宏論,使本港輿論界為之譁然,董橋表示驚詫及難以認同。此舉固然不足為訓,但他畢竟沒有出任過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對此不可略過。至於其武俠小說作品,能否列入嚴肅文學,愚意以為見仁見智,無需深究。但不能不承認其文字功夫一流!
寒山碧:我只是不贊成對金庸過度吹捧而已。
Sk Cheung:實際上連吹捧也不應該。過度當然更不妥。但金庸本人也不見得開心度日--其長子自殺,續娶者出身灣仔杜老誌,頗有竊竊私議者。原不能跟梁羽生琴瑟和諧家庭幸福相比!
MauChiWang 繆熾宏:https://gbcode.rthk.hk/TuniS/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1692&fbclid=IwAR3OqI56pJLh7nN-WKMSi6RFTQxxf-UmAUtD-10pKi--3hsPbplnWPd92Cc
寒山碧:謝謝繆兄分享。
MauChiWang 繆熾宏:寒老:20多年前,我曾用曲筆寫了對查良鏞的看法。
譚志強:查良鏞學長有很多不同面目,主要的有三個,首先是作為報紙老闆的查良鏞,基本上是一個孤寒利獨的文化商人,和香港其他老闆無異。其次是在親共反共之間反覆橫跳,最後舐共至死的典型政客豺狼庸。再次才是曾經寫成14部暢銷武俠小說的作家金庸,但是,這個金庸在寫完"鹿鼎記"停筆之後就已經死亡了。
寒山碧:同意所論。
MauChiWang 繆熾宏:
在我內文中,曾引逑這一段:“ 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司馬文武在《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的序言中,有一段這樣說話:「近代中國大陸出現不少傑出記者,尤其在對日戰爭前後。不過,他們在戰亂政治漩渦中,逐一淹沒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記者,都無法對不義的社會,長期保持超然與客觀的態度,因此早晚必定被捲入去他們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根本無法找到新聞記者的生存空間,他們被迫選擇立場,結果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
事實上,在《明報》與查良鏞報人成長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機會可以置身於國共鬥爭夾縫外,也是最有可能辦一份真正「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報章的。大抵上,筆者認為查良鏞在創造、鞏固與令《明報》成長上,他的確是中外傑出報人,但是,也許這亦是人性的本質或弱點。在八十年代查良鏞參與草委一役上,間接令到《明報》踏上政治「不歸路」,同時他也揚言《明報》是他個人私器,這種種言論及政治行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與報業》一書中,張圭陽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銳及批判的分析,相信會令其作品更有說服力。 ” ……由這角度去看,林行止的成就比查良鏞更高了,因林懂得運用香港曾幾何時有的政治中立之優勢去獨立评論兩岸四地的政局,雖然到今天,一切均已經不復存在了。
寒山碧:林行止有大陸生活經驗,對老共沒有幻想。
譚志強:寒山碧 老查幫紅媒打工多年,老爸被共產黨無罪槍決,後來咪一樣對共產黨有幻想,舐共至死,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和有無在大陸生活經驗,關係不大。
譚志強:寒山碧 現在海外不少小粉紅、五毛黨、 側翼、第五緃隊,還有台灣的“紅統份子”,亦是如此。
寒山碧:譚志強 曾在大陸生活必知老共本性。其餘則是選擇不同。
(寒山碧臉書2023年2月19日)
从《金庸与报业》看报人与政治互动微妙关系
缪炽宏 新观点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 / 市场研究及资讯科经理
资深新闻工作者张圭阳,最近出版其在香港大学毕业哲学博士(历史学)论文改编后的作品,名为《金庸与报业》,该书可算是在近十年香港新闻界内尚佳之作。
《金庸与报业》是张圭阳以近代史之方法,去叙述、评估与分析《明报》,自一九五九年创刊后,在查良镛领导下发展史实,从而综合查良镛在香港过去半个世纪中,如何在转变中的动荡政局,香港九七回归所呈现的政治与经济现象、分治的海峡两岸现实,以及香港民主发展中,《明报》与查良镛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及取舍。
本文重点是透过该书去看上一代报人与当时政治气候互动的微妙关系,藉此检视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报人,能否有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人格与报格?香港又是否有这些土壤?未来的前景又是如何?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
《明报》的诞生与成长,可算是标志香港在过去五十年的种种宏观与微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推而广之,也概栝了整个中国的变化。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清楚交代了查良镛透过《明报》所呈现的四种精神,分别为(一)高举儒家思想、(二)强烈民族意识、(三)崇尚自由及(四)反战。在查良镛一代报人身涯中,以下事迹可以说是有其极代表性意义:
第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期间,因国内难民涌入,《明报》在报导与评论难民问题上,与本港左派立场南辕北辙,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查良镛展开与《大公报》的笔战,当时查良镛是这样写着:「金庸出身自《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道路......」
第二,一九六四年十月,随着中国在新疆试爆核子弹成功,查良镛以反核及赞成全面毁灭核弹,遭新华社以「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回应。
第三,在文革期间,《明报》及查良镛以大量来自国内「原始资料」(即红卫兵的编印小报),去分析国内局势,彭真何时下台,以及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明报》发表多篇由查良镛撰写社评,如《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五月十八日)、《英国的香港政策》(五月十九日)等去分析当时中国政局。
第四,在整个八十年代,当香港面对前途问题,在香港回归中国道路与进程上,查良镛更扮演举足轻重角色,他分别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组港方组长。其间,香港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政制辩论。此外,在广东省内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也引起社会及中港关系强烈分化。其时,《明报》及查良镛均积极参与其内。曾任《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有这样体会:「社评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个社评主笔的事情,而是查良镛许可的立场。如香港的直选,民主建设的速度等问题,都要与他讨论后才执笔,要经过潘粤生(总编辑)修改,或是经徐东滨(主笔)修改,才能见刊。」
由此可见,在八十年代期间,查良镛对《明报》立场控制,在上述问题上,非常严格,也难怪他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他有权表达他的看法。「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政治立场与取舍
在上述所阵列四个时期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年仅三十五岁的查良镛于一九五九年创立《明报》之际,从一开始,正如张圭阳分析,查良镛希望《明报》最初是一份小报,走偏锋,并利用一些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去吸引读者。随着岁月的冲击,中国政局转变,也在查良镛早年敢于与左派划清界线,因而成为中港台及全球华人尊崇对象与报刊。《明报》因而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知识份子的报刊,也赢得很高的清誉。笔者认为,这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藉此奠定查良镛成为全球华人地区报界典范。
但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是间接成为晚年查良镛失误或晚节不保的潜藏原因。查良镛曾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上摆设食物的圆盘」。《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他常被讥笑批评为机会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左摇右摆的墙头草。笔者认为,除了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间查良镛可歌可泣的表现,查良镛最大失误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绝中国政府邀请加入基本法草委会及其后一连串中方为收回香港所设置的委员会或担任其智囊。假使在这期间,查良镛能断然拒绝这些被统战的机会,他往后成就或留给后世作榜样,可能会有更高的评价。这即是说,查良镛作为上一代知识份子报人,最终未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独立个体,实属有点可惜,这个观点,也一直是笔者详细阅读《金庸与报业》一书时,一直在脑海中徘徊思考的课题。当然,像这样「主观」的结论,查良镛也未会认同。
新闻界独立政权以外
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司马文武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的序言中,有一段这样说话:「近代中国大陆出现不少杰出记者,尤其在对日战争前后。不过,他们在战乱政治漩涡中,逐一淹没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记者,都无法对不义的社会,长期保持超然与客观的态度,因此早晚必定被卷入去他们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根本无法找到新闻记者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选择立场,结果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明报》与查良镛报人成长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机会可以置身于国共斗争夹缝外,也是最有可能办一份真正「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章的。大抵上,笔者认为查良镛在创造、巩固与令《明报》成长上,他的确是中外杰出报人,但是,也许这亦是人性的本质或弱点。在八十年代查良镛参与草委一役上,间接令到《明报》踏上政治「不归路」,同时他也扬言《明报》是他个人私器,这种种言论及政治行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张圭阳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锐及批判的分析,相信会令其作品更有说服力。
当前香港正充满着无数的市民怨气与不满,在发生香港大学「钟庭耀事件」后,特区首长或透过其高级私人助理干预学术自由,香港知识份子的腰骨有多硬,新闻界能否独立政权以外而去监察政府,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都是与本文主题有着密切关系,也值得新闻界及每一位港人所深思反省的。此时此刻,香港更需要有一个独立于政权、敢于批判政权的声音。
(《香港電台網站‧傳媒透視》2000年8月15日)
西城兄說,「要尊敬金庸」,我本來不想談,但網絡上已有人談及,我也不妨談談自己的看法。面書本來就是讓人們閒聊臧否人物的平台。
談到查先生,我認為必須分開前後,一個是獲鄧小平接見之前的查先生,另一個是獲鄧小平接見之後的查先生。
前一個查先生我是非常尊敬的,甚至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明報》和《明報月刊》是我重要的精神糧食。查先生獲鄧小平接見後我對他的敬佩打了折扣,特別是他風塵撲撲跑到深圳覲見許家屯,提出《雙查方案》後,我對他的尊敬大幅削減。俟後,他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博士導師之後,他的多番言行,令我對他的尊敬蕩然無存。因為後一個查先生完全否定了令我所敬佩的前一個查先生。
西城兄對查先生是近觀,或許有發現查先生未為人知的優點,我對查先生是遠望,我所望見的也是大家所望見的,故不妨公諸於眾。下文是我記述與查先生唯一見面。
--------------------------------------------------------------------------
※金庸請鐵凝吃飯我作陪
我不記得是那一天,反正是鐵凝在港短短這幾天內,我忽然接潘耀明電話,說金庸先生邀請鐵凝和我吃晚飯,我只考慮片刻便答應了。我當然知道,查良鏞老闆要宴請的是鐵凝主席不是我,只因為鐵凝是我的客人,潘耀明又得通過我去邀請鐵凝,不好意思把我甩開吧?也順便邀請了我。我與金庸雖然有點芥蒂,曾著文批評過他, 但君子坦蕩蕩,沒有甚麼是需要迴避的。
我與《明報》及查良鏞先生欠點緣份,在開辦自己文化公司之前我是一個自由投稿者,可是卻從未向《明報》投稿,而《明報》〈自由談〉卻是最多大陸仔投稿的園地。等到我自己創辦《東西方》之後卻與《明報》發生些許磨擦,前面已有述及,在此不贅。而2003年,我又寫了一篇談論金庸的小文──《譽之極至,謗必隨之──冷眼看金庸小說的爭論》,這篇小文是編者力邀下才產生的。我在文首說:「本文題目,原是三年前席間的閒談。1999年12月我在大陸參加陳序經(前嶺南大學校長、暨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副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全盤西化的提倡者)學術研討會。宴會上一位來自北京的學者端木正教授(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女兒端木美(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突然問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對北京近日關於金庸小說的爭論有何看法?我當時說:『這是沒有必要的爭論,譽之極至,謗必隨之』,並簡略談了我的觀點。原無意訴之文字,但《香江文壇》主編漢聞兄一再邀約,衹好應命。」
我在這篇小文裡說:「《金庸傳》的作者譽他為寫『寫武俠小說的『世界第一俠筆,寫社論的香江第一健筆』有沒有問題呢?絕對沒有問題……《信報》老闆林行止先生,雖然也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但兩人沒有太大矛盾。……查、林兩君只是一前一後,互相輝映,並且相信林君也無意與『查大俠』於香江論筆,爭第一。金庸小說爭論的由來,不是出於他的小說,而是出自小說之外的因素。……金庸被抬舉已久從八十年代起……溢美之聲從未間斷,有沒有問題呢?絕對沒有問題……金庸的武俠小說被吹捧為『文學革命』,金庸也被吹捧成『文學大師』……而且高踞中國現代文學第四把交椅,把茅盾等都壓下去。……甚至有人建議提名金庸參選諾貝爾文學獎。……一波又一波的吹捧抬舉,金庸已儼然成為國際級『文學大師』了……這一來令文學界頓然省悟,他們可不是鬧着玩的,是來真的的了。於是再也不敢掉以輕心,這才出現鄢烈山的《拒絕金庸》和王朔的《我看金庸》等『批金』文章,一場金庸小說爭論也由此而起。』」
至於我自己的觀點毋須贅言,只須看小標題可知。文章的小標題是:〈武俠小說終歸祇是武俠小說〉,〈金庸所獲得的尊榮是單純由武俠小說帶來的嗎?〉〈大陸的文學批評的墮落與進步〉」。武俠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有很大隨意性,無論甚麼事情都可以突然而來,毋須鋪墊,讀過文學系,遍讀世界名著的人,很難接受武俠小說是嚴肅的文學,金庸是頂級的「文學大師」這種說法。故我在最後一節說:「聖人曰:『大位不以智取』,我認為大名也不可智取,像『文學大師』之類大名如以智謀取之,往往適得其反,即使得逞於一時,往往也為日後帶來罵名。此即譽之極至,謗必隨之也!……十年後,大陸的文學界有人對金庸『文學大師』表示『拒絕』,把武俠小說從文學的神龕上搬下來,放回坊間通俗的攤檔上,顯示大陸的文學批評已有長足的進步,我感到欣然。」
2005年江蘇的電視台訪問我的朋友原南京大學副校長董健先生,就大陸把金庸的武俠小說編入中學教科書的問題問他的看法,董健不僅公開表示反對,而且還引述我跟他在閒談時說過的批評大陸過度捧承金庸的話。事後他還打長途電話給我詳述其事,談了將近一個小時。董健與我同齡,是中國極少數敢言的知識份子之一,我們有不少共同的觀點。
我上述言行,相信金庸是清楚的,金庸想宴請鐵凝順便請了我,可能是他的大度,我的應邀自然不是為了吃一餐,而是顯示我的坦蕩。我不記得晚宴是在那間酒樓,只記得我得我到酒店去接鐵凝,聯袂赴約。進入席間才知道晚宴只有查先生、查夫人、潘耀明、鐵凝和我。席間的談話內容我已不記得了,只記得大家都盡量避開談小說和武俠小說,我是盡量低調,不亢不卑,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見查先生。鐵凝離港前雖然她的秘書跟我交換電話和電郵地址,但她返京後我再也沒有跟她聯繫,所以我跟鐵凝不能算朋友,只是工作關係。
(寒山碧臉書2021年2月19日)
讀者回應:
Sk Cheung:
竊以為對金庸不必苛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雙查方案作為一家之言,後來成為不少草委的共識,對其中是非也無需較真。整個《基本法》就是一道緊箍咒,港人就算是孫悟空再生也無法逃脫。現在的《國安法》更加直截了當!再者,金庸應張浚生之邀出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並擔任博士生導師,其間發表媒體應像解放軍那樣聽黨指揮的宏論,使本港輿論界為之譁然,董橋表示驚詫及難以認同。此舉固然不足為訓,但他畢竟沒有出任過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對此不可略過。至於其武俠小說作品,能否列入嚴肅文學,愚意以為見仁見智,無需深究。但不能不承認其文字功夫一流!
寒山碧:我只是不贊成對金庸過度吹捧而已。
Sk Cheung:實際上連吹捧也不應該。過度當然更不妥。但金庸本人也不見得開心度日--其長子自殺,續娶者出身灣仔杜老誌,頗有竊竊私議者。原不能跟梁羽生琴瑟和諧家庭幸福相比!
MauChiWang 繆熾宏:https://gbcode.rthk.hk/TuniS/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1692&fbclid=IwAR3OqI56pJLh7nN-WKMSi6RFTQxxf-UmAUtD-10pKi--3hsPbplnWPd92Cc
寒山碧:謝謝繆兄分享。
MauChiWang 繆熾宏:寒老:20多年前,我曾用曲筆寫了對查良鏞的看法。
譚志強:查良鏞學長有很多不同面目,主要的有三個,首先是作為報紙老闆的查良鏞,基本上是一個孤寒利獨的文化商人,和香港其他老闆無異。其次是在親共反共之間反覆橫跳,最後舐共至死的典型政客豺狼庸。再次才是曾經寫成14部暢銷武俠小說的作家金庸,但是,這個金庸在寫完"鹿鼎記"停筆之後就已經死亡了。
寒山碧:同意所論。
MauChiWang 繆熾宏:
在我內文中,曾引逑這一段:“ 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司馬文武在《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的序言中,有一段這樣說話:「近代中國大陸出現不少傑出記者,尤其在對日戰爭前後。不過,他們在戰亂政治漩渦中,逐一淹沒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記者,都無法對不義的社會,長期保持超然與客觀的態度,因此早晚必定被捲入去他們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根本無法找到新聞記者的生存空間,他們被迫選擇立場,結果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
事實上,在《明報》與查良鏞報人成長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機會可以置身於國共鬥爭夾縫外,也是最有可能辦一份真正「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報章的。大抵上,筆者認為查良鏞在創造、鞏固與令《明報》成長上,他的確是中外傑出報人,但是,也許這亦是人性的本質或弱點。在八十年代查良鏞參與草委一役上,間接令到《明報》踏上政治「不歸路」,同時他也揚言《明報》是他個人私器,這種種言論及政治行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與報業》一書中,張圭陽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銳及批判的分析,相信會令其作品更有說服力。 ” ……由這角度去看,林行止的成就比查良鏞更高了,因林懂得運用香港曾幾何時有的政治中立之優勢去獨立评論兩岸四地的政局,雖然到今天,一切均已經不復存在了。
寒山碧:林行止有大陸生活經驗,對老共沒有幻想。
譚志強:寒山碧 老查幫紅媒打工多年,老爸被共產黨無罪槍決,後來咪一樣對共產黨有幻想,舐共至死,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和有無在大陸生活經驗,關係不大。
譚志強:寒山碧 現在海外不少小粉紅、五毛黨、 側翼、第五緃隊,還有台灣的“紅統份子”,亦是如此。
寒山碧:譚志強 曾在大陸生活必知老共本性。其餘則是選擇不同。
(寒山碧臉書2023年2月19日)
从《金庸与报业》看报人与政治互动微妙关系
缪炽宏 新观点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 / 市场研究及资讯科经理
资深新闻工作者张圭阳,最近出版其在香港大学毕业哲学博士(历史学)论文改编后的作品,名为《金庸与报业》,该书可算是在近十年香港新闻界内尚佳之作。
《金庸与报业》是张圭阳以近代史之方法,去叙述、评估与分析《明报》,自一九五九年创刊后,在查良镛领导下发展史实,从而综合查良镛在香港过去半个世纪中,如何在转变中的动荡政局,香港九七回归所呈现的政治与经济现象、分治的海峡两岸现实,以及香港民主发展中,《明报》与查良镛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及取舍。
本文重点是透过该书去看上一代报人与当时政治气候互动的微妙关系,藉此检视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报人,能否有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人格与报格?香港又是否有这些土壤?未来的前景又是如何?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
《明报》的诞生与成长,可算是标志香港在过去五十年的种种宏观与微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推而广之,也概栝了整个中国的变化。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清楚交代了查良镛透过《明报》所呈现的四种精神,分别为(一)高举儒家思想、(二)强烈民族意识、(三)崇尚自由及(四)反战。在查良镛一代报人身涯中,以下事迹可以说是有其极代表性意义:
第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期间,因国内难民涌入,《明报》在报导与评论难民问题上,与本港左派立场南辕北辙,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查良镛展开与《大公报》的笔战,当时查良镛是这样写着:「金庸出身自《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道路......」
第二,一九六四年十月,随着中国在新疆试爆核子弹成功,查良镛以反核及赞成全面毁灭核弹,遭新华社以「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回应。
第三,在文革期间,《明报》及查良镛以大量来自国内「原始资料」(即红卫兵的编印小报),去分析国内局势,彭真何时下台,以及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明报》发表多篇由查良镛撰写社评,如《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五月十八日)、《英国的香港政策》(五月十九日)等去分析当时中国政局。
第四,在整个八十年代,当香港面对前途问题,在香港回归中国道路与进程上,查良镛更扮演举足轻重角色,他分别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组港方组长。其间,香港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政制辩论。此外,在广东省内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也引起社会及中港关系强烈分化。其时,《明报》及查良镛均积极参与其内。曾任《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有这样体会:「社评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个社评主笔的事情,而是查良镛许可的立场。如香港的直选,民主建设的速度等问题,都要与他讨论后才执笔,要经过潘粤生(总编辑)修改,或是经徐东滨(主笔)修改,才能见刊。」
由此可见,在八十年代期间,查良镛对《明报》立场控制,在上述问题上,非常严格,也难怪他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他有权表达他的看法。「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政治立场与取舍
在上述所阵列四个时期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年仅三十五岁的查良镛于一九五九年创立《明报》之际,从一开始,正如张圭阳分析,查良镛希望《明报》最初是一份小报,走偏锋,并利用一些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去吸引读者。随着岁月的冲击,中国政局转变,也在查良镛早年敢于与左派划清界线,因而成为中港台及全球华人尊崇对象与报刊。《明报》因而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知识份子的报刊,也赢得很高的清誉。笔者认为,这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藉此奠定查良镛成为全球华人地区报界典范。
但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是间接成为晚年查良镛失误或晚节不保的潜藏原因。查良镛曾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上摆设食物的圆盘」。《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他常被讥笑批评为机会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左摇右摆的墙头草。笔者认为,除了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间查良镛可歌可泣的表现,查良镛最大失误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绝中国政府邀请加入基本法草委会及其后一连串中方为收回香港所设置的委员会或担任其智囊。假使在这期间,查良镛能断然拒绝这些被统战的机会,他往后成就或留给后世作榜样,可能会有更高的评价。这即是说,查良镛作为上一代知识份子报人,最终未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独立个体,实属有点可惜,这个观点,也一直是笔者详细阅读《金庸与报业》一书时,一直在脑海中徘徊思考的课题。当然,像这样「主观」的结论,查良镛也未会认同。
新闻界独立政权以外
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司马文武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的序言中,有一段这样说话:「近代中国大陆出现不少杰出记者,尤其在对日战争前后。不过,他们在战乱政治漩涡中,逐一淹没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记者,都无法对不义的社会,长期保持超然与客观的态度,因此早晚必定被卷入去他们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根本无法找到新闻记者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选择立场,结果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明报》与查良镛报人成长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机会可以置身于国共斗争夹缝外,也是最有可能办一份真正「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章的。大抵上,笔者认为查良镛在创造、巩固与令《明报》成长上,他的确是中外杰出报人,但是,也许这亦是人性的本质或弱点。在八十年代查良镛参与草委一役上,间接令到《明报》踏上政治「不归路」,同时他也扬言《明报》是他个人私器,这种种言论及政治行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张圭阳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锐及批判的分析,相信会令其作品更有说服力。
当前香港正充满着无数的市民怨气与不满,在发生香港大学「钟庭耀事件」后,特区首长或透过其高级私人助理干预学术自由,香港知识份子的腰骨有多硬,新闻界能否独立政权以外而去监察政府,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都是与本文主题有着密切关系,也值得新闻界及每一位港人所深思反省的。此时此刻,香港更需要有一个独立于政权、敢于批判政权的声音。
(《香港電台網站‧傳媒透視》2000年8月15日)
2021年2月16日 星期二
許定銘:細說神州五十年 ──序歐陽文利的《販書追憶》
神州主人歐陽文利兄囑我為他的新著《販書追憶》寫序,非常高興。雖未見其書,不過心裡明白,知道我必會第一時間捧讀此書,今次能趕在出書前先睹為快,故一口答應。前此在網路上讀新亞主人蘇賡哲兄的《舊書商回憶錄》,餘味無窮,不知是否已在整理排印中?如能與文利兄的《販書追憶》同時面世,當是香港舊書壇的盛事!
《販書追憶》其實是文利兄的回憶錄,全書收文二十三篇,大致可分為兩部分,此中〈十三歲入行〉、〈管舊書〉、〈派到廣州、上海訂貨〉……到〈創業苦與樂〉及〈眾人相助買下地舖〉等十一篇,記述了他從小學未畢業即入行、苦讀、奮鬥、開業到成為舊書業翹楚的經過,和一般成功人士的傳記無異,都是由血淚與毅力累積而成的成就;所不同的是「舊書」這個行業比較特別,一向不受人注意,大部分讀者都未接觸過,題材獨特,引人入勝,細讀之更見趣味無窮。
另一部分則是香港舊書業,自一九五零年代起,至現在的實際情況;歐陽文利與神州舊書店,一直是這個時期的重鎮,見證了香港舊書業的盛衰,《販書追憶》不僅僅是文利兄的回憶錄,還是一部擲地有聲的香港舊書業史!
此中我特別有興趣的是〈舊書業購貨經驗〉、〈港島到九龍的舊書攤〉、〈「出口書莊」的出現〉和〈出口書莊的興衰〉幾篇。舊書業最重要的是貨源,很多談買賣舊書的文章,談到進貨時多只說到康記和三益,頂多再加上何老大的書山,少有像歐陽文利說得那麼細緻的,如卑利街斜路的李伯,鴨巴甸街口的「大光灯」……等,不僅清楚地指出書店的所在地,人物的外號,賣些甚麼書,都似賬單的清晰,可見其真實性,尤其吸引。
談舊書的文章中,我首次在《販書追憶》讀到「書莊」。事實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書莊」是甚麼?其實「書莊」即是「莊口」。舊日有些稱為「莊口」的出入口形式公司,專門由本地把生活必須品運到多華人聚居的南洋、歐美等城市,書,是精神食糧,也是必須品之一,所以間中也有運書的,不過不多,而且多為通俗的流行書,但間中也有例外。一九七零年代我就曾經在某莊口中購得近二百本無名氏的絕版書《露西亞之戀》,是我個人大批買賣舊書的首次經驗。
歐陽文利口中的「書莊」,就是指純以書籍出口,賣給外地圖書館的樓上專門店。這些書莊雖然專做外埠生意,但長年累月也有不少貨源積在店內,故此,也做門市的。只要你知道門路上到去,他們也會讓你在架上選購,因為那些多是大批買回來時的配角,所以價錢也不貴,我就曾在某書莊以三十元買過葉紫的《豐收》(上海奴隸社,一九三五) ,此書十分罕見,畢生從未遇見另一册。
在歐美圖書館大批到香港搶購舊書的七、八十年代,這種書莊是相當多的,歐陽在書中提到:智源書局、萬有圖書公司、遠東圖書公司、實用書局、集成圖書公司……等,他不但清楚地講述書店的經營模式,連老闆的出身都知之甚詳,實在難得。
我是一九七二年首到神州的,當時店內絕版罕見的新文學作品還不少,我如獲至寶,次次有斬獲,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端木蕻良的《江南風景》只賣二十,是平靚正。北京賣舊書的大亮,專賣中國新文學絕版舊書,是我每次上京買舊書必到之處。而在《販書追憶》中提到,大亮年年來港,到神州貨倉購貨甚多;我從大亮手中所得新文學書,相信不少亦來自神州,可見神州的貨倉是個舊書的聚寶盆。
一九六五年創業的神州,至今已超過五十五年歷史,拙文題為〈細說神州五十年〉是取其整數。事實上,神州如今已是第二代接手,下次再有人談神州,隨時是:〈舊書業的百年老店神州〉了!
──2021年2月
《販書追憶》其實是文利兄的回憶錄,全書收文二十三篇,大致可分為兩部分,此中〈十三歲入行〉、〈管舊書〉、〈派到廣州、上海訂貨〉……到〈創業苦與樂〉及〈眾人相助買下地舖〉等十一篇,記述了他從小學未畢業即入行、苦讀、奮鬥、開業到成為舊書業翹楚的經過,和一般成功人士的傳記無異,都是由血淚與毅力累積而成的成就;所不同的是「舊書」這個行業比較特別,一向不受人注意,大部分讀者都未接觸過,題材獨特,引人入勝,細讀之更見趣味無窮。
另一部分則是香港舊書業,自一九五零年代起,至現在的實際情況;歐陽文利與神州舊書店,一直是這個時期的重鎮,見證了香港舊書業的盛衰,《販書追憶》不僅僅是文利兄的回憶錄,還是一部擲地有聲的香港舊書業史!
此中我特別有興趣的是〈舊書業購貨經驗〉、〈港島到九龍的舊書攤〉、〈「出口書莊」的出現〉和〈出口書莊的興衰〉幾篇。舊書業最重要的是貨源,很多談買賣舊書的文章,談到進貨時多只說到康記和三益,頂多再加上何老大的書山,少有像歐陽文利說得那麼細緻的,如卑利街斜路的李伯,鴨巴甸街口的「大光灯」……等,不僅清楚地指出書店的所在地,人物的外號,賣些甚麼書,都似賬單的清晰,可見其真實性,尤其吸引。
談舊書的文章中,我首次在《販書追憶》讀到「書莊」。事實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書莊」是甚麼?其實「書莊」即是「莊口」。舊日有些稱為「莊口」的出入口形式公司,專門由本地把生活必須品運到多華人聚居的南洋、歐美等城市,書,是精神食糧,也是必須品之一,所以間中也有運書的,不過不多,而且多為通俗的流行書,但間中也有例外。一九七零年代我就曾經在某莊口中購得近二百本無名氏的絕版書《露西亞之戀》,是我個人大批買賣舊書的首次經驗。
歐陽文利口中的「書莊」,就是指純以書籍出口,賣給外地圖書館的樓上專門店。這些書莊雖然專做外埠生意,但長年累月也有不少貨源積在店內,故此,也做門市的。只要你知道門路上到去,他們也會讓你在架上選購,因為那些多是大批買回來時的配角,所以價錢也不貴,我就曾在某書莊以三十元買過葉紫的《豐收》(上海奴隸社,一九三五) ,此書十分罕見,畢生從未遇見另一册。
在歐美圖書館大批到香港搶購舊書的七、八十年代,這種書莊是相當多的,歐陽在書中提到:智源書局、萬有圖書公司、遠東圖書公司、實用書局、集成圖書公司……等,他不但清楚地講述書店的經營模式,連老闆的出身都知之甚詳,實在難得。
我是一九七二年首到神州的,當時店內絕版罕見的新文學作品還不少,我如獲至寶,次次有斬獲,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端木蕻良的《江南風景》只賣二十,是平靚正。北京賣舊書的大亮,專賣中國新文學絕版舊書,是我每次上京買舊書必到之處。而在《販書追憶》中提到,大亮年年來港,到神州貨倉購貨甚多;我從大亮手中所得新文學書,相信不少亦來自神州,可見神州的貨倉是個舊書的聚寶盆。
一九六五年創業的神州,至今已超過五十五年歷史,拙文題為〈細說神州五十年〉是取其整數。事實上,神州如今已是第二代接手,下次再有人談神州,隨時是:〈舊書業的百年老店神州〉了!
──2021年2月
2021年2月11日 星期四
潘惠蓮:香港第一種「三毫子小說」:《小說報》的創刊號重見天日
《小說報》創刊號的封面。(鳴謝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館批准拍攝)
1957年12月27日《工商晚報》
香港第一種「三毫子小說」:《小說報》的創刊號「出土」了!
原來它長期藏於一個鮮為人知的角落。筆者因去年十月發表了〈香港的「三毫子小說」何時誕生?〉一文,有緣發現它藏身之處,幾經折騰,終於讓這個封存已久的創刊號,得以重見天日!。
上次借助美國的解密檔案和香港的舊報章廣告,查證香港第一種三毫子小說《小說報》約於1955年2月1日面世,由虹霓出版社(The Rainbow Press)出版。第一期刊登了著名小說家俊人的作品〈金碧露〉。俊人原名陳子雋,即六七暴動期間,傳誦一時的反共健筆——萬人傑。
早期的《小說報》現時甚為罕見,上次撰文前,曾查找香港各圖書館,及請教多名藏書家及研究人員,均未見〈金碧露〉的影蹤。最早一期得見的《小說報》,是馬來西亞藏書家蕭永龍提供的第三期:歐陽天撰寫的〈彩筆奇緣〉。文章發表後約兩個月,獲「HK History」群組成員: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前任館長楊國雄whatsapp知會,香港大學圖書館的特藏館存有《小說報》的創刊號。
筆者初閱此訊息,深表懷疑,因早已從該館的電腦目錄檢索,並無發現。於是再查一次,在《小說報》的電腦目錄內,依然沒看到創刊號,只有幾本1960年代出版的《小說報》,這些已經找出來看過。但楊國雄先生再發來一張照片,顯示一頁紙本目錄上,有《小說報》創刊號的記錄,並指該創刊號已微縮成菲林收藏,著我向港大圖書館特藏館主管查詢。
港大圖書館不是已全面採用電腦目錄檢索嗎?還有紙本目錄?帶著多個疑問到特藏館查詢。適逢聖誕長假期剛過,館長仍在休假中,服務枱的館員同樣利用電腦目錄替我查找,同樣沒有發現,也不知道另有紙本目錄。館員於是電郵向館長查詢。
已移居加拿大的楊國雄先生指出,館存的那份《小說報》創刊號,原是已故名報人吳灞陵(1904-1976)的珍藏之一。他少年時期已開始致力收集香港各種報刊的創刊號及特刊。吳灞陵去世後,時任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館長的楊國雄,經好友聯繫,向他的遺屬購得這批珍藏,存放館中,並在此基礎上繼續收集。由於數量龐大,楊國雄在1990年退休時,整理工作仍在進行中。到1997年,才由他的繼任人完成紙本目錄,及把千多項創刊號及特刊藏品製成微縮菲林。之後的情況,他並不清楚。(筆者註: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專門收集香港史料,現屬特藏館管理)
電郵查詢發出後兩天,才得悉那批創刊號和特刊,仿如遺世獨立地隱藏館中,與現行的電腦目錄系統掛不上鈎。《小說報》創刊號竟不在《小說報》的電腦目錄中顯示,而是另外藏於「香港報紙創刊號」的欄目內,此欄目有菲林多達十數卷,內藏千多項創刊號及特刊,全無電腦記錄,需靠助一冊紙本目錄,才能看到這千多個項目的名稱,及查出藏品在哪卷菲林內。這種狀況,前線館員毫不知情。而該冊紙本目錄,此際無故在架上失蹤了多天,經館方兩輪搜索才尋回!
得見菲林內微縮的〈金碧露〉,只是黑白影像,且不清晰。於是申請查看、量度和掃描原件。隔日,館方取出原件,但僅供翻閱和量度,我退而求其次,要求只用手機拍攝封面,亦需再寫信申請。筆者鍥而不捨,再電郵詳述理據,終於獲批,前後折騰了16日,才令〈金碧露〉的原貎重見天日。
這種情況,已向特藏部館長反映,容後另文再論。先來看看〈金碧露〉的樣貎,一共12版,長濶度是39cm x 27cm,跟早已見過的第三期,同屬略長8開類。筆者從舊報找到1957年12月27日《工商晚報》的一篇宣傳稿,介紹《小說報》由此日出版的第59期開始,革新版面,改善紙張編排。相信就是從這期起,《小說報》由略長8開,縮小至8開(約37.5cm x 26cm)。目前在收藏家手上可見的第60期:劉以鬯的〈椰樹下之慾〉,便是8開。
內容方面,〈金碧露〉描述1954年間,一對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男女,在相識短短兩個半月內的際遇。男主角姓秦,任職教師,某次跟同事到灣仔舞廳消遣,認識了別具氣質的舞小姐金碧露。交談後,得知大家同是畢業於上海的滬江大學,便十分投契,自此成為摯友。
金碧露原名宋玉華,在大學修讀英國文學,畢業後與上海財經官員羅海沙結婚,育有一子。豈料中共上台後,羅海沙迅即投靠新政權,逐漸變得奸險詭詐,在三反、五反政治運動中,迫害一直栽培善待他的叔父。金碧露不願與他共同生活,便帶著兒子到香港另尋出路,但人浮於事,只得以伴舞維生。
秦在大學修讀法律,來港四年,依然找不到本行工作。他已婚,妻子在廣州因要處理父親留下的家產,遲遲不願南下香港和他團聚,結果中共掌權後,不獲准離境,夫妻從此分隔兩地。
金碧露在舞場上認識了商人黃超群,計劃和他結婚。沒料到一名聲稱是他太太的女子到舞場向金碧露動粗,並警告別再纏擾黃超群。金碧露才驚覺黃超群一直謊說妻子已離世。
秦為了鼓勵金碧露,在自己任教的學校為她覓得一份教職,原本以為她可從此開展新生活。可是,她在上海的丈夫突然來到香港,威脅要帶走兒子。金碧露慌忙把兒子送到秦的居所暫住,之後便獨自回家。不久,被發現離奇墮樓身亡。秦到殮房認屍時,遇到也來認屍的黃超群。黃表示那名在舞場向金碧露動粗的女子,根本不是他的太太,而是單戀他的表妹,蓄意破壞他和金碧露的感情。
黃、秦二人都認為金碧露墮樓的原因可疑,於是向警方提出疑點,包括金碧露死前曾被丈夫羅海沙恐嚇。不久,黃超群資助金碧露七歲的兒子往台灣升學,完成金碧露生前的願望。而秦在廣州的妻子,此時成功偷渡來港,和他團聚。至此故事終結,但金碧露的死因仍沒有揭盅,到底是他殺還是自殺?
這個可歸屬言情小說類的作品,頗為曲折,集愛情、親情、政治、懸疑、新聞素材於一身。過往有文章指陳子雋在六七暴動爆發後,才以「萬人傑」這筆名撰寫反共文章,之前一直以「俊人」的筆名發表言情小說。但從〈金碧露〉這篇小說可見,早於五十年代,陳子雋的言情作品,已有批判中共的元素。
此外,筆者上篇文章提及:《小說報》面世時,便以招牌字句「一本名作家的小說,一份報紙的價錢」作宣傳。這說法隨著〈金碧露〉的「出土」,亦需加以修正。因為《金碧露》的封面下方,印著四句宣傳語:「一流作家、一流作品、最低代價、全篇讀完」,而不是第三期封面下方呈現的字句:「一本名作家的小說,一份報紙的價錢」。這兩句話其後一直沿用,卻非《小說報》面世時採用。至於是由第二期、還是第三期開始採用,則要待第二期:南宮搏撰寫的〈水東流〉「出土」,才能確定。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協理李卓賢指出,《小說報》創刊號〈金碧露〉重現,為三毫子小說何時誕生、三毫子小說因何出現、從俊人到萬人傑的寫作軌跡等議題,提供了重要物證,對研究1950年代的香港文學,包括該中心的「三毫子小說研究計劃」,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Samplex微批文學媒體計劃》2021年2月7日,另見Linda Pun臉書2021年2月11日。)
(此圖由玷句輝提供,見Linda Pun臉書2021年2月11日。)
2021年2月7日 星期日
悼黃牧(之二)
沈西城:老友記走了!
九十年年代初,我跟馬龍合編《花花公子香港版》,他管美術、我掌文字,名家如林,倪匡、古鎮煌皆在網中。倪老大寫科幻、古小弟教收藏。先前,我在《明周》看到他教人投資的文章,立意與眾不同, 眼力不在股票、地產,而重手錶、墨水筆等小物品。碰巧手錶、墨水筆,皆我所好,有意結交,遂託人向他索稿,慨然俯允,《花花公子》從此有了古鎮煌。
刊了幾期,反應熱烈,發稿費時,我致電約他來編輯部聊聊。首夏清和,一陣春風把阿古吹來,身材適中,樣貌平凡,卻擁有一對智慧眼睛,談起投資文章,他說「我們做人要有後着,不然晚年難過。」本為大公司CEO,四十後退休,專職遊覽,範圍有二:一是遊遍天下名山大川,一覽春色;二是徜徉於收藏世界,以錶和墨水筆為尊。我也喜藏此二物,不知名山在前,肆言道心得。阿古聽了大半,插嘴道:「你的收藏眼光不壞,不重名氣而在趣味。」說對了,我第一塊錶,是媽媽送我的梅花嘜;第二塊女友餽贈,是依波路,孖公仔,有寓意。阿古說挺喜歡機械錶,每早上鍊頂享受。至於墨水筆,我選德國拿美,阿古有同嗜。談得投契,臨走時,不再稱我沈先生,易口叫「老友記」。自此常見面,我只知阿古好收藏,不知他心有大學問。用本名黃牧寫樂評,精專絕倫,輒與我談,我薄馬勒,寧取當拿,我的音樂水平,僅止於小調。阿古搖頭嘆息「你條友仔,唉!」大不以為然。論學問,我遠遠比不上他,可有一樣,我當上他老師,一講到男女,阿古定必恭恭敬敬,洗耳恭聽。某日,匆匆來看我,苦着臉,問「老友記,你得救我!」原來阿古滬上行,碰到酒店禮賓小姐,少女豐姿,此豸為絕,一見傾心。於是乎週五出發,週日回港,戮力追求,時日飛逝,苦無成果,於是下馬問道。別以為阿古有歪意,實求美人跟他吃一頓法國燭光晚餐。我苦無言語相慰,僅以微笑報之。有點失落,頹唐而還,從此少再找我。阿古去世矣,我有良言告:女人不必苦纏,不Like你,追也枉然。老友記,你可聽到?望釋懷!
(《蘋果日報》2021年1月31日)
邵頌雄:逍遙一生
黃牧(左圖)傳給作者的一張照片,是他於成都開設私房菜餐館「草堂樂府」的一角。餐館有展櫃擺放他收藏的唱片、紅酒、古董筆、古董相機等。
過去一星期,私下與黃牧的一些舊雨新知多有聯繫,每天也讀到悼念他的文章。其中一篇,提到黃牧遊經柏林之時,倏地給路德維兄發一個短訊,稱呼這位德國通為「柏林先生」,問路到柏林愛樂樂團森林音樂會場地,還不拘泥長幼輩份,向路兄直言「您可跟我上上課,說說森林舞台的擴音處理嗎?」。讀到此處,頓起音容宛在之感,久久難以釋懷。黃牧說話一向多精準而生鬼的形容詞,與其玩世不恭的人生取態,相映成趣。
未識其人,總會把黃牧臆想為一名樂癡。交往多年,發覺其實不然,因為他有興趣鑽研的事物太多。晚年的他固然是世上數一數二的旅遊癡和芭蕾癡,早年的他也是紅酒癡、筆癡、錶癡、相機癡、美食癡。有次他到寒舍作客,閒談之際聊到書法,原來他年輕時也曾是書法癡,對各種碑帖興致勃勃地談了一個晚上。擁抱偌大森林,當然不會只見音樂這片樹葉。他癡而不着、執而不迷,有興趣的都可以玩得刁鑽精專,甚至提早退休來全職遊玩,但玩過便算,拿得起亦放得下,貫轍其遊戲人間的抱負。
有朋友以為「古鎮煌」為其筆名、「黃牧」才是本名,其實兩者都是筆名。早幾年他送了一部由他編纂的英文小書給我,用的又是另一筆名,還解釋過名字背後令人忍俊不禁的含義。該書以機場過境旅客為對象,黃牧謂想不到甫推出便賣斷市,之後一再翻印,輕鬆賺了一筆供他耍樂。他寫文章也不失遊戲本色,分享經驗之餘,往往不乏嬉笑怒罵,印象尤深的,是他寫收藏古董筆的一篇,說到某品牌時,忍不住口便加上一句「有趣的是,這商標今天成了甚至『不大會寫字』的一些暴發戶的一種身分象徵」;談到古董錶,則寄語「古董錶之精,正是因為它是『費時失事』的產品。藝術的價值,正是『花許多時間做極少的事!』」。
林道群先生早日於社交媒體上登出金庸寫給董橋的「手諭」,當中提到「像黃牧的文章,以輕鬆活潑之筆調談知識性內容,相信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藝術評論文章,任何愛好者都可以寫,但故作高深卻又錯漏百出者則在在可見,反而深入淺出、閒話家常而有導引入門的實際效果,可謂只此一家,是為金庸慧眼識其與眾不同之處。這種文風,令他的著作不賣弄、不吹捧,而具有綜觀整門學問、簡述箇中發展、比較今昔轉變、細析名家風格等的善誘功能。
我最早擁有的黃牧著作,是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音樂演藝名家》。如今翻出,讀見篇首序言:「我在香港的刊物上寫有關古典音樂的文章,轉眼間似乎已寫了六七年。在這段日子裏,無論寫的是甚麼,我的目標始終一貫——希望藉此誘導更多的年輕人,去掌握能夠大大改善生活質素的機會。 …… 要做到真正愛音樂,一定還得有相當的音樂修養。而要有修養,其實別無他途:只有多聽,多讀書,多研究。」環顧香港年輕一輩的樂評人,近日紛紛撰文追悼這位樂評前輩,不少提到最初建立對古典音樂的認識和興趣,就是讀黃牧的文字而來。這份撰寫樂評的初衷種子,三十年後得見開花結果,桃李滿枝。
如今他大部分的樂評結集早已絕版。幾年前曾替他把新作與舊文稍加整理後,他將之重新編排,上冊以《現場:聽樂四十年》的書名出版,內容為他親身聆聽一眾頂級大師現場演奏的紀錄。下冊題為《傳奇:二十世紀的樂壇巨匠》,以導賞上世紀古典音樂黃金時代的大師風範為主,但由於種種原因未有付梓,文稿幽幽地寄存我的電子郵箱內,誠為可惜。他常笑言,撰寫樂評是經濟效益最低的寫作,是故也已擱筆多年不寫,若非遇上我們圍內好幾個樂癡,也未必重拾這方面的著述、與眾樂樂。
如此寓癡愛於寫作的人生,晃眼四十餘年。每次與他匆匆一聚,總見他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趕往下一個目的地。他通過藝術而體會的人生,猶如歌劇般如幻如化,你不一定會同意他的口味或觀點、他也不會如臨大敵般竭力辯斥,就任由他討厭的丑角或英雄隨着劇情登場或退場。
黃牧最鍾愛的作曲家,是理查.史特勞斯,尤愛他的歌劇《玫瑰騎士》、《阿拉貝拉》等,及其遺作《最後四首歌》。敘舊之時,談到酣暢淋灕之處,他往往按耐不住輕吟一段,還會眉飛色舞地細說哪一位歌唱家在該段旋律的處理如何精妙。那份對生命的熱忱、對生活的追求,令人動容。
逍遙幾十載,忽然自他的舞台從此隱佚,尤教諸友好懷念。他今年月初給我的最後電郵,其中有言「2020 can’t be worse especially for me. But surely 2021 will be bette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nd family.……」。今天翻看他的書時,不意見到一段他翻譯晚年理查.史特勞斯的一封書信:「一年容易又除夕……我的生機恐怕已經斷絕了。現在,我要自問為甚麼上天讓我生在這個世界上:這個除了我和家人和一、二位好友之外,一切都這麼討厭、這麼冷淡的世界。我希望你和尊夫人新年愉快,過的不是我在這個『刑室』裏過的這種新年。」所說竟與給我的電郵如出一轍,讀之茫然。
(《蘋果日報》2021年2月6日)
九十年年代初,我跟馬龍合編《花花公子香港版》,他管美術、我掌文字,名家如林,倪匡、古鎮煌皆在網中。倪老大寫科幻、古小弟教收藏。先前,我在《明周》看到他教人投資的文章,立意與眾不同, 眼力不在股票、地產,而重手錶、墨水筆等小物品。碰巧手錶、墨水筆,皆我所好,有意結交,遂託人向他索稿,慨然俯允,《花花公子》從此有了古鎮煌。
刊了幾期,反應熱烈,發稿費時,我致電約他來編輯部聊聊。首夏清和,一陣春風把阿古吹來,身材適中,樣貌平凡,卻擁有一對智慧眼睛,談起投資文章,他說「我們做人要有後着,不然晚年難過。」本為大公司CEO,四十後退休,專職遊覽,範圍有二:一是遊遍天下名山大川,一覽春色;二是徜徉於收藏世界,以錶和墨水筆為尊。我也喜藏此二物,不知名山在前,肆言道心得。阿古聽了大半,插嘴道:「你的收藏眼光不壞,不重名氣而在趣味。」說對了,我第一塊錶,是媽媽送我的梅花嘜;第二塊女友餽贈,是依波路,孖公仔,有寓意。阿古說挺喜歡機械錶,每早上鍊頂享受。至於墨水筆,我選德國拿美,阿古有同嗜。談得投契,臨走時,不再稱我沈先生,易口叫「老友記」。自此常見面,我只知阿古好收藏,不知他心有大學問。用本名黃牧寫樂評,精專絕倫,輒與我談,我薄馬勒,寧取當拿,我的音樂水平,僅止於小調。阿古搖頭嘆息「你條友仔,唉!」大不以為然。論學問,我遠遠比不上他,可有一樣,我當上他老師,一講到男女,阿古定必恭恭敬敬,洗耳恭聽。某日,匆匆來看我,苦着臉,問「老友記,你得救我!」原來阿古滬上行,碰到酒店禮賓小姐,少女豐姿,此豸為絕,一見傾心。於是乎週五出發,週日回港,戮力追求,時日飛逝,苦無成果,於是下馬問道。別以為阿古有歪意,實求美人跟他吃一頓法國燭光晚餐。我苦無言語相慰,僅以微笑報之。有點失落,頹唐而還,從此少再找我。阿古去世矣,我有良言告:女人不必苦纏,不Like你,追也枉然。老友記,你可聽到?望釋懷!
(《蘋果日報》2021年1月31日)
邵頌雄:逍遙一生
黃牧(左圖)傳給作者的一張照片,是他於成都開設私房菜餐館「草堂樂府」的一角。餐館有展櫃擺放他收藏的唱片、紅酒、古董筆、古董相機等。
過去一星期,私下與黃牧的一些舊雨新知多有聯繫,每天也讀到悼念他的文章。其中一篇,提到黃牧遊經柏林之時,倏地給路德維兄發一個短訊,稱呼這位德國通為「柏林先生」,問路到柏林愛樂樂團森林音樂會場地,還不拘泥長幼輩份,向路兄直言「您可跟我上上課,說說森林舞台的擴音處理嗎?」。讀到此處,頓起音容宛在之感,久久難以釋懷。黃牧說話一向多精準而生鬼的形容詞,與其玩世不恭的人生取態,相映成趣。
未識其人,總會把黃牧臆想為一名樂癡。交往多年,發覺其實不然,因為他有興趣鑽研的事物太多。晚年的他固然是世上數一數二的旅遊癡和芭蕾癡,早年的他也是紅酒癡、筆癡、錶癡、相機癡、美食癡。有次他到寒舍作客,閒談之際聊到書法,原來他年輕時也曾是書法癡,對各種碑帖興致勃勃地談了一個晚上。擁抱偌大森林,當然不會只見音樂這片樹葉。他癡而不着、執而不迷,有興趣的都可以玩得刁鑽精專,甚至提早退休來全職遊玩,但玩過便算,拿得起亦放得下,貫轍其遊戲人間的抱負。
有朋友以為「古鎮煌」為其筆名、「黃牧」才是本名,其實兩者都是筆名。早幾年他送了一部由他編纂的英文小書給我,用的又是另一筆名,還解釋過名字背後令人忍俊不禁的含義。該書以機場過境旅客為對象,黃牧謂想不到甫推出便賣斷市,之後一再翻印,輕鬆賺了一筆供他耍樂。他寫文章也不失遊戲本色,分享經驗之餘,往往不乏嬉笑怒罵,印象尤深的,是他寫收藏古董筆的一篇,說到某品牌時,忍不住口便加上一句「有趣的是,這商標今天成了甚至『不大會寫字』的一些暴發戶的一種身分象徵」;談到古董錶,則寄語「古董錶之精,正是因為它是『費時失事』的產品。藝術的價值,正是『花許多時間做極少的事!』」。
林道群先生早日於社交媒體上登出金庸寫給董橋的「手諭」,當中提到「像黃牧的文章,以輕鬆活潑之筆調談知識性內容,相信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藝術評論文章,任何愛好者都可以寫,但故作高深卻又錯漏百出者則在在可見,反而深入淺出、閒話家常而有導引入門的實際效果,可謂只此一家,是為金庸慧眼識其與眾不同之處。這種文風,令他的著作不賣弄、不吹捧,而具有綜觀整門學問、簡述箇中發展、比較今昔轉變、細析名家風格等的善誘功能。
我最早擁有的黃牧著作,是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音樂演藝名家》。如今翻出,讀見篇首序言:「我在香港的刊物上寫有關古典音樂的文章,轉眼間似乎已寫了六七年。在這段日子裏,無論寫的是甚麼,我的目標始終一貫——希望藉此誘導更多的年輕人,去掌握能夠大大改善生活質素的機會。 …… 要做到真正愛音樂,一定還得有相當的音樂修養。而要有修養,其實別無他途:只有多聽,多讀書,多研究。」環顧香港年輕一輩的樂評人,近日紛紛撰文追悼這位樂評前輩,不少提到最初建立對古典音樂的認識和興趣,就是讀黃牧的文字而來。這份撰寫樂評的初衷種子,三十年後得見開花結果,桃李滿枝。
如今他大部分的樂評結集早已絕版。幾年前曾替他把新作與舊文稍加整理後,他將之重新編排,上冊以《現場:聽樂四十年》的書名出版,內容為他親身聆聽一眾頂級大師現場演奏的紀錄。下冊題為《傳奇:二十世紀的樂壇巨匠》,以導賞上世紀古典音樂黃金時代的大師風範為主,但由於種種原因未有付梓,文稿幽幽地寄存我的電子郵箱內,誠為可惜。他常笑言,撰寫樂評是經濟效益最低的寫作,是故也已擱筆多年不寫,若非遇上我們圍內好幾個樂癡,也未必重拾這方面的著述、與眾樂樂。
如此寓癡愛於寫作的人生,晃眼四十餘年。每次與他匆匆一聚,總見他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趕往下一個目的地。他通過藝術而體會的人生,猶如歌劇般如幻如化,你不一定會同意他的口味或觀點、他也不會如臨大敵般竭力辯斥,就任由他討厭的丑角或英雄隨着劇情登場或退場。
黃牧最鍾愛的作曲家,是理查.史特勞斯,尤愛他的歌劇《玫瑰騎士》、《阿拉貝拉》等,及其遺作《最後四首歌》。敘舊之時,談到酣暢淋灕之處,他往往按耐不住輕吟一段,還會眉飛色舞地細說哪一位歌唱家在該段旋律的處理如何精妙。那份對生命的熱忱、對生活的追求,令人動容。
逍遙幾十載,忽然自他的舞台從此隱佚,尤教諸友好懷念。他今年月初給我的最後電郵,其中有言「2020 can’t be worse especially for me. But surely 2021 will be bette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nd family.……」。今天翻看他的書時,不意見到一段他翻譯晚年理查.史特勞斯的一封書信:「一年容易又除夕……我的生機恐怕已經斷絕了。現在,我要自問為甚麼上天讓我生在這個世界上:這個除了我和家人和一、二位好友之外,一切都這麼討厭、這麼冷淡的世界。我希望你和尊夫人新年愉快,過的不是我在這個『刑室』裏過的這種新年。」所說竟與給我的電郵如出一轍,讀之茫然。
(《蘋果日報》2021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