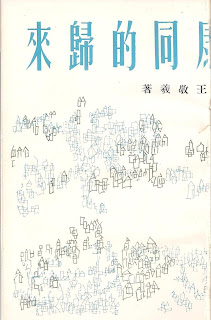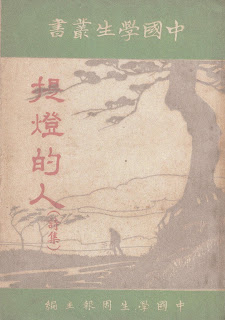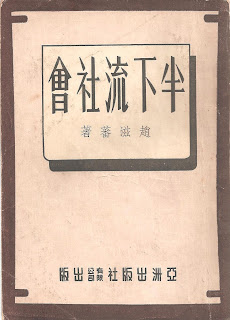許定銘
閱報得知王敬羲(一九三三~二OO八)在溫哥華因癌病逝世,深以為憾!消息來得突然,就像一九八O年忽聞司馬長風(一九二O~一九八O)離世般錯愕。我把王敬羲和司馬長風拉在一起,因為我和王敬羲的交往,是因司馬而起的。
二OOO年我從多倫多回港,賦閑在家學電腦,完成了萬多字的舊稿〈情書專家章衣萍和他的作品〉寄給《純文學》,王敬羲迅即刊登,還約我見面。他說以前讀過我寫司馬長風的文章,以為我是與司馬同輩的文人,因他與司馬有點姻親關係,想從他的朋友中收集一些材料,以便作研究之用;沒想到我與司馬是忘年交,差了一代人,甚至比王敬羲也年輕十多歲!雖然我們年齡有差距,但一見如故,交往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純文學》停刊,我又找到了新工作,大家都忙,才漸漸少了來往。
王敬羲是江蘇青浦人,一九五O年代初於本港培正中學就讀時已開始寫作,後來到台灣師大升學,更熱心寫作,在夏濟安主持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並在台灣出版了《七星寮》(台南大業書店,一九五五)、《聖誕禮物》(台北明華書局,一九五五)、《掛滿獸皮的小屋》(台中光啓出版社,一九五七)、《青蛙的樂隊》(台中光啓出版社,一九五八)等多部作品。
王敬羲一九六O年代初回港,在尖沙咀某大厦的六樓開了間「文藝書屋」,專售台灣出版的文藝書籍,是本港樓上書店的鼻祖。當年能買到台版純文學創作的書店,就只有旺角的「友聯」和王敬羲的文藝書屋。那時候台灣的「文星書店」正大展拳脚,除了出版《文星雜誌》,還大量出版《文星叢刊》;文藝書屋就像文星的代理般,好書來得又快又暢銷,如今我的書架上還擺著朱西寧的《鐵漿》(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三)和司馬中原的《加拉猛之墓》(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三),即購於此。後來王敬羲甚至把暢銷的文星書在本港重印,出版了港版《純文學》和《南北極》月刊,又辦正文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童年與同情》、《懷璧集》、林太乙的《丁香遍野》、任畢明的《閒花集》、王敬羲的《歲月之歌》……等,都是水平甚高的作品。文藝書屋聲名大噪,所有文藝青年均視此書屋為文學中心!
王敬羲的小說中,最為人重視的是短篇小說集《康同的歸來》,此書於一九六七年在台灣文星書店及香港正文出版社同時出版,如今大家見到的,是「正文版」,扉頁有王敬羲給筆者的簽贈手蹟,三十二開本,一四三頁,收〈黑髮〉、〈女房客〉、〈冬天的故事〉、〈鬼婚〉……等十二個短篇,王敬羲在〈自序〉中說,雖然書中有長達二萬五千字,極適宜用作書名的〈開花的季節〉,但他最後還是決定以〈康同的歸來〉作書名,因為這篇小說很有紀念價值。
一九六五年,王敬羲到愛奧華修讀文學寫作碩士,是他寫作的高峯期,《康同的歸來》中的十二篇小說,都是這時期的作品,尤其是〈康同的歸來〉,它不僅是王敬羲赴美後的首篇傑作,它還刊登在《文星雜誌》最後的一期上,對他來說,這篇小說記錄了某階段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階段的開始,意義重大!
〈康同的歸來〉寫的是台灣學生留美的故事。窮學生康同拋下寡母,帶着僅夠一年的生活費赴美國中部的小城讀博士,一年終結後到紐約苦幹尋下學年的生活費。正當費用已籌得七七八八之際,忽聞母親急病入院,康同連忙把錢寄回去讓母親做手術,卻仍救不了老人的性命。自此,遭遇坎坷的康同自甘墮落,沉醉於煙酒賭的世界而不再讀書,五年後空手回到台北去……。
留學生故事是一九六O年代的熱門話題,在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中,王敬羲卻讓我們接觸失敗的背面!
王敬羲與友聯出版社的關係密切,他不單中學時期已為友聯所出的《中國學生周報》寫稿,他的小說《多彩的黃昏》(一九五四)和《選手》(一九五五),都是友聯出版的。一九六O年代,友聯在新加坡有純文藝月刊《蕉風》,王敬羲經常為它寫稿,我手上有本中篇小說《久違陽光的人》(新加坡蕉風出版社,一九六四),即是《蕉風》所出的單行本。
《久違陽光的人》薄薄的,僅三十頁,約二萬字,時代背景是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寫十四歲的中學生江家瑞,因給老師取渾號「狗腿子」而被趕出校。他在家中停學一年,冷眼觀察身邊家人的生活,深感缺乏家庭温暖。後來得二叔之助,轉讀另一中學,家人又因他成績跟不上而替他請補習老師,江家瑞像「久違陽光的人」重見光明一樣,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久違陽光的人」江家瑞的年紀與王敬羲相若,故事題材可能即來自他本人的童年往事,或同學的遭遇,埋藏心底十多年後寫成小說,注入了深厚的情感,雖然也寫得不錯,但若要與《康同的歸來》中小說相比,則是有一段距離的。此書沒有定價,可能是附於《蕉風》內的贈品,不受注意,此所以連王敬羲私人網站上的〈王敬羲作品編目〉中也不列,值得一提並記述,以免湮沒。
我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國學生周報》作通訊員,因熱心推廣,在向同學徵訂中得獎,獲贈小書若干冊,此中有秋貞理(司馬長風) 的《北國的春天》、《段老師的眼淚》和多人合著的詩集《提燈的人》。
《提燈的人》﹙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一九五四﹚是本集體創作詩集,是《中國學生叢書》之一。從編印的話中知道,書中的作品都是先在《周報》上發表過,其後才選輯成書的。此書雖然只有六十八頁,卻包括了五十六位詩人的六十二首作品。作為書名的〈提燈的人〉,就是王敬羲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時的詩作:
一個沉睡的夜,王敬羲當然不單單在寫一個提燈的人趕夜路的情景,而是表達了那提點他、引導他前進的先行者﹙明燈﹚和個人要走的方向。寓意深遠,難怪編者以此作為書名。學習寫作初期,我們往往都會作多方面的嘗試,然後慢慢地向某點集中寫下去;王敬羲的小說讀得多,詩,還是第一次讀到哩!
一盞淒涼的燈,
青藍的燈火,湖水中的星,
在漫長的路上搖曳……
× ×
燈,照不出影,
和路上的坎坷。
但,藉漸弱的燈火,
更遠的探尋,行進。
× ×
提燈的人,佇望——
有一分光,佇望,到天明。
王敬羲在本港從事文學工作超過半世紀,從寫作到開書店、到出版雜誌,貢獻良多;寫作〈提燈的人〉時,他絕對想不到後來自己會成為這個南方小島上的「提燈者」,為後來的文藝青年照亮他們坎坷難走的黑路!
永別了,「提燈的人」,你走好!走好!
──寫於二OO八年十月
十一月刊於《城市文藝》
王敬羲遺作:《校園與塵世》
許定銘
二OO八年十月,閱報得知香港小說家王敬羲(一九三三~二OO八)在溫哥華因腸癌逝世,深以為憾!我寫了悼念文章〈《提燈的人》王敬羲〉,發表於十一月份的《城市文藝》,記述我和他交往的經過,並以他寫於一九五O年代的一首短詩〈提燈的人〉,表揚他半世紀以來為香港文化作出的貢獻。拙文最後的一段是這樣寫的:
王敬羲在本港從事文學工作超過半世紀,從寫作到開書店、到出版雜誌,貢獻良多;寫作〈提燈的人〉時,他絕對想不到後來自己會成為這個南方小島上的「提燈者」,為後來的文藝青年照亮他們坎坷難走的黑路!不久,旅居溫哥華的陳浩泉給我來電,說是王敬羲的家人打算為他出一本遺作,並問我願不願意把〈《提燈的人》王敬羲〉附錄於書後,我當然答應。事隔半年,《校園與塵世》(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二OO九)的樣書便送來了。
永別了,「提燈的人」,你走好!走好!
《校園與塵世》是王敬羲生前,繼《囚犯與蒼蠅》、《搖籃與竹馬》、《船與島嶼》後的自選集,內文原先只有散文與小說兩部分,但因趕不及出版就撒手西去,他的家屬接手整理,附錄了四篇紀念性的文章,成為第三部分,還寫了前言,並由王敬羲夫人劉秉松後記,長子王人鈞設計封面,自選集第四種《校園與塵世》便成了王敬羲遺作!
一本作家的自選集當然以作品為主,因為這都是作者本人滿意之作。《校園與塵世》的散文部分收〈從舊愛到新歡〉、〈上流社會的娼奴〉、〈白色恐怖‧林海音‧《純文學》〉、〈沙化上的老者〉、〈我的父親母親〉、〈濛濛的月亮〉、〈散步‧溫哥華〉和〈廣州雜憶〉等八篇。看王敬羲的安排,他是有意把他一生各段階,選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一總結。這裏有論文、雜寫,也有內心感情的抒發;有戀愛、家庭的温馨,辦雜誌、出版遭到的挫折,也有台北、香港、温哥華、廣州各地生活的記錄。尤以後期〈廣州雜憶〉一組雜寫,記述了台北和廣州的兩城故事,寫中國小鯢,老人和女孩,最能接觸他寂寞的晚境!
王敬羲在天津出生,在香港、台北及美國渡過他的學習生涯,家人早年已定居溫哥華,他卻樂於香港、溫哥華、廣州間三地來去奔波近三十年,令人費解。不過,讀過本書的剖白後,你大概可以尋到蛛絲馬跡,明白他的流浪心態。
小說部分收〈一個陌生人〉、〈潮退時〉、〈張奇慧的故事〉、〈舊地重臨〉、〈昨夜〉和〈開花的季節〉等六篇,應以後三篇為重點。
在本書的附錄裏,有葉維廉寫於一九六八年,論王敬羲小說的〈弦裏弦外〉,主要談他小說裏的「雕塑意味」,推崇王敬羲小說裏的「弦外之意」及「立體性」,即以這三篇小說來分析。
〈舊地重臨〉寫一位被派到台北工作的「白領」,對他來說,台北是舊地重臨,他回想到過去的生活……;〈昨夜〉則寫女舍監應付幾個寄宿生的故事。葉維廉認為王敬羲的小說,能在沉悶、瑣碎、平凡的叙述裏「出奇」,在庸俗裏求一刻精神的領悟而顯出「靈性」。他要依從日常事件發展的進程慢慢述說,卻在結尾給人突發的奇想。此舉實乃文學作品中能令人回味,深具延伸力的弦外之意。
而在具實驗意味的〈開花的季節〉中,王敬羲則摒棄了小說中的平面叙述,用幾件平行發展,卻又極之類似的故事,演繹了蓮麗和梅麗姊妹倆不同的命運,組成了一個立體。故事以七章組成:
第一章:這裏講述一個名叫小蓮的舞女的故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香港)這篇用七個片段組成的小說,葉維廉認為它:
第二章:這裏講述一個名叫梅麗的女學生的故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香港)
第三章:一個男孩子的覺醒(一九五三年九月廿日 香港)
第四章:一個成年男子的覺醒(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香港)
第五章:一個流浪漢的覺醒(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 台南)
第六章:一個地痞的覺醒(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台北)
第七章:月亮和梅麗(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台北)
用故事多線的延伸,看着它們偶然的交合為一個立體的圓形就好像現象多線的延展,偶然結為一個八面玲瓏的光球。(頁一五七)是王敬羲巔峰之作。葉維廉是王敬羲深交超過半世紀的老友,也只有他能深深明白到王敬羲創作的苦心和小說背後的心意!
《校園與塵世》的附錄中,除了葉維廉的〈弦裏弦外〉,還有許定銘的〈《提燈的人》王敬羲〉、顧媚的〈過客〉和楊權的〈昨日的文壇鬥士〉,三篇都是王敬羲過世後的悼念文章,尤其最後一篇,記述了王敬羲晚年在廣州生活的情況,極具參考價值。
王敬羲辭世後,悼念的文章很多,《校園與塵世》中僅選三篇,是不足以代表我們對他的懷念,王敬羲的老同學馬森,在《聯合報》上發表的〈一個不應遺忘的小說家〉,就是一篇不應遺漏的好文章。不過,我們也明白到,作為王敬羲自選集的《校園與塵世》,附錄是不應份量過重的。因此,我們深切地期待會有一冊《王敬羲紀念集》面世,我覺得:〈王敬羲年譜〉和他最後寫成的〈一個癌症患者的獨白〉是絕對不能缺少的!
──寫於二OO九年九月
十一月刊於《城市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