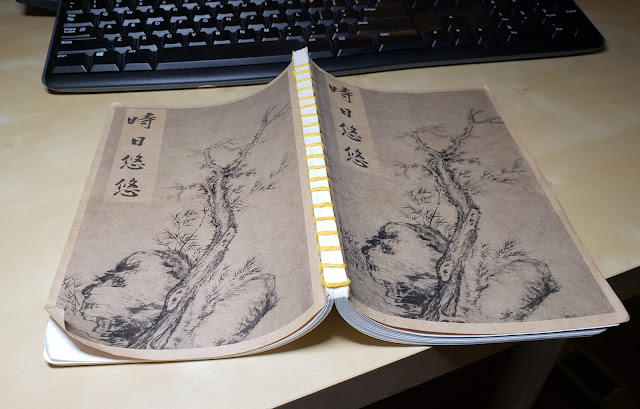陳韻文
作者提供相片
黃念欣在讀到「有話直說」與「記憶中的事實」之後,寫了一篇長文「編劇與小兵」。文章末段她如是寫道:「小兵之美,全在不計較。能夠欣賞《小兵敘曲》的陳韻文,寫『有話直說』也肯定不是為了計較。那為甚麼還要寫呢?正正也是因為能夠欣賞《小兵敘曲》的人,必然明白,藝術的本質,就是表達,講一個好故事。陳韻文提醒我們一切心血與感情皆有來歷,美好事物值得堅持與留痕。」
小兵的不計較究竟是什麼?那得看《小兵敘曲》Ballad of a Soldier。看了,自然可以感到那難以言表的「不計較」。很迂迴吧。黃念欣動我以「小兵」之美,乍看不過寥寥數語,其實語重心長,傳喻我的不計較之美盡在不言中。
恰好這幾年,一位香港人都熟悉的人物,與我天各一方生活幾十年之後,近年再聯繫,多以電郵通訊,只見面一次,飯敘兩個小時而已。我因為要在《偏偏我遇見》這本回憶錄裏寫她,搜羅了許多資料,加上從前接觸的印象,以為已經熟悉,哪想到,這幾年才真正往深裏認識她;才欣賞到那發自內心的瀟灑,那不能模仿的風度,而那,正是我所了解的「不計較」。
那午後,剪了一頭短髮寫意離開髮廊,久違的劉天蘭恰恰傳來短訊,問我在哪,幾時回港,說芳芳找我。好哇!短髮清爽我抬頭,陽光無限好!劉天蘭說:芳芳要拍攝一特輯,其中有《撞到正》,負責人文念中會訪問你,會和你聯絡,也想幫你做個特輯。不!不出鏡,因為人醜怪。至於訪問,坦白說,當年趕得急,編劇對劇本不滿意。編劇也覺得導演差勁。這部戲若果沒有芳芳幕前幕後撐持,肯定死火。我問劉天蘭:你教我講真話抑或講假話?她不假思索回道:當然講真話。可我決意不講真話也不講假話。乾脆不要訪問。乾脆請芳芳吃飯。
2017年2月下旬的一個下午,近三時下機,好不容易趕得及六時半的飯約。全部人已經到齊。《撞到正》的美指李樂詩,關錦鵬嚴浩許鞍華和她的摯友,芳芳從上午的會議至下午的訪問兼錄影,直撐着,甚至早到半小時。雖倦,可仍透着她特有的生命魅力。雖然失聰,她可是由始至終留意每一個人的唇語,遇不明白即請劉天蘭寫給她看。見我拿嚴浩尋開心,她活活潑潑說了一次又一次:我哪時再見你們倆,讓我再見你們倆。我看看嚴浩,這傢伙還是吃了幾十斤豬油的模樣。嘿!當年我們促膝忖劇本,我和芳芳你一言我一語嘻嘻哈哈靈感似戲院小賣部的爆穀。嚴浩那雙大眼越瞪越呆,終於牛咁聲負氣一爆:「至憎啲女人多多聲氣。」芳芳和我相視失笑,碌兩碌眼恨無鬚,有鬚吹吹該多好。
轉頭見身側的許鞍華騎騎笑。不由得想到跟她和芳芳坐在半島酒店構思《撞到正》的故事。那陣子芳芳很緊張,晚飯後來電話,說O'Henry的溫情故事。隔一個晚上看看Edgar Allan Poe能不能給我靈感。講兩講心散散說要嫁給張正甫。
酒店大堂茶座裏我和她講UFO,說:「有幾種外星人。有早早來投胎,快高長大後,一日,失驚無神被摑醒,即郁。另一種經特種訓練,派來竊竊潛伏,聽候任務。又有一批臨危受命來勢洶洶攪攪震。」我語音未落,芳芳機伶伶眼珠一轉拂一下光滑膝蓋,嗔聲:「鬼唻㗎!」扯口大氣我抬頭,乍覺那辰光的大堂人傑地靈。之後,我講戲班下南洋的紅船,她嫌成本重,改為落鄉班。聞落鄉二字。我聯想到無綫舊同事說曾祖賣假藥,害死了患痢疾的過境士兵。從此家中男丁總不見命長。如此這般摸出個非要娶芳芳不可的阿B。如此這般拼拼湊湊拼出《撞到正》。在一旁的許鞍華要嘛沒出現,要嘛騎騎笑。可是若干年後。訪問中被問到,她說「我講了個鬼故事。他們大讚好……」昔日讀到那段文字,我不禁哼聲。想芳芳,她大概也一笑置之。不計較。
回頭說那夜飯後。樂極生悲。只因一星期內連飛三次長途。航機上不愛睡覺愛煲戲。結果隔天一早急急召車送自己去醫院。折騰半天好不容易躺下。美術指導文念中似乎算準了時間來句話,說攝影師和助手都準備好。問我在哪兒訪談。我說我在醫院裏呀。病牀上兀自想芳芳怎麼想。說不出的歉疚。《撞到正》是芳芳的Baby,我這人是不是太牛了。
出院後,許鞍華只顧要我助手翻譯她的電影故事,只顧給我看第四部劇本。悶聲不響我收下。幾次三番她的摯友問劇本好不好。沒有給他答案。縱有任何不滿都悶在心裏。那是2017年。那年的12月,她接受訪問。插我捅我的話我到2019年的3月才知曉。我至今不明白,既然把我說的那麼不濟,怎麼這些年一而再要我幫她看劇本。怎麼這回插我捅我這回又叫我幫忙。
2018年農曆初二,香港早晨六時,她突然傳來幾句英文:「恭賀新禧,多謝給我幾個頂瓜瓜劇本,開始我的事業。」我現在回想起,十分心寒。
2018年黃愛玲突然辭世。我趕回香港扶靈。約芳芳在愛玲上山那天飯敘,結果因為要在一天半天內趕兩篇寫愛玲的長文,下午四時多交稿後,以為瞌睡一會才趕赴六點鐘約會,結果睡過了頭,半夜才醒。我連連道歉,芳芳怎說呢:「約吃飯都是小事,你晚一點到或趕不來,準有你的原因……咱倆以後誰也別為了遲回信說抱歉,要不然太生分了。」有回見我為小事困擾,她說:「不打緊,由它去。我陪你一起被利用,不是挺好嗎。」
2019年春節前,加拿大嚴寒,她送暖,說呢:「想你了。你會來香港過舊曆新年嗎?要是來的話,我想請你年三十晚來我家打邊爐。劉天蘭也會來。希望你一切安好。」「記憶中的事實」見報當天,3月16號,久未來訊的芳芳驀地來短語:「想你了,希望你天天開心。」
(原刊香港《蘋果日報》2019年3月30日,這裏刊出的是作者修訂稿,見陳韻文臉書2019年4月4日。)
陳韻文︰
2015年,香港電影資料館為好幾位編劇特別安排一連串講座,名之為「編劇的困惑」。我把《小兵敘曲》放在我講座的第一晚。年輕時不只一次看這電影。至2015年,人生的歷練,工作的經驗令我看的更深;我看到導演Chukhra與編劇Ezhov 如魚得水的合作,看到他們藉這作品寓意於善良、真誠、與寛容,以及對人情人性最起碼的寄望。哪想到幾年後的今天,我乍見人醜惡的一面,對我已付出的善良忠誠與寛容不願再有任何寄託、在我對人情人性極度存疑的困惑時刻,黃念欣,感激妳把《小兵敘曲》帶回來。妳話中提到「小兵」的「不計較」,讓我別有領悟。這隔空的交談實在甚有意義,我銘心感謝。
既然提到「小兵」,我想起 1960年康城電影節,影評人形容《小兵敘曲》為「不調和交響樂中的寧謐音符」。這令我連想到舒伯特的第八交響曲,開始一節已經予人山雨欲來的感覺。許多大指揮家演繹這「未完成交響樂」,我獨愛小澤征爾。另外是艾遜伯赫指揮法蘭克福廣播電台的交響樂團。2016年在德國Reingall,Eberbach修道院開幕之時現場錄映的演奏。
Man Hung Stephen Sze︰你提的應該叫《小兵之歌》(Ballad of a Soldier)吧?這是在斯大林死後,一片社會祥和氣氛下,應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風格,敢於道二次大戰中蘇聯人民所蒙受的苦難,傷痛和仳離,抹走了過去戰事電影的英雄主義,當然還有憂傷淒美的俄羅斯音樂及蘇聯的風格化攝影!
陳韻文︰Man Hung Stephen Sze,是史太林死後幾年,赫魯曉夫治下THAW時期的作品,導演曾上戰塲受傷兩次……很好的電影。這片子有譯為《小兵敘曲》又有譯為《小兵之歌》,現在叫敘曲因要接日昨黃念欣女士那篇文章用的名字。
(陳韻文臉書2019年3月26日)
編劇與小兵
文、圖︰黃念欣
小兵與辮子女孩。(圖:黃念欣)
名編劇陳韻文在專欄文章〈有話直說〉與〈記憶中的事實〉中,與名導演許鞍華商榷幾部名電影的創作意念及其來源,雖然娛樂版以「被陳韻文點名指摘 許鞍華封口停是非」為題報道,但我絕無「花生友」心態,真心覺得這兩篇文章好好看。今時今日,筆戰文章而能於人有益的,恐怕不多,這次金風玉露一相逢,是例外。
文章一次過讓我們重溫《瘋劫》、《投奔怒海》、《桃姐》、《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的細節及來龍去脈,每個電影細節都包含着念念不忘,寫到人的心坎裏。《瘋劫》中的衣裳竹、家傳皮箱道具、趙雅芝與張艾嘉的眼神;《投奔怒海》在難民營的資料蒐集,以及《桃姐》、《黃金時代》中陳韻文可能不以為然的地方,都清楚坦白。不用說還有兩晚通宵趕起《投奔怒海》的劇本,清晨七時交許鞍華去電影公司開會的那種彪悍勁,真是十分有型。
前輩的合作關係,電影複雜的製作過程,我都不曉,合該閉嘴。真正讓我想舊事重提朝花夕拾一番的,是好幾年前陳韻文大駕光臨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偕小思老師等一同看《中國學生周報》的資料庫,她談到的一齣蘇聯電影《小兵敘曲》(Ballad of a Soldier)。她說是對她影響甚深的一部電影,我馬上請教如何影響得深?她就說:「你睇吖,你睇咗先吖。」結果當晚看完,果真令人淚流滿面,不只潤澤心靈,更能刺激思考。這次「陳許編導」事件,竟讓我不期然又再想起它。
《小兵敘曲》屬蘇聯電影中「解凍時期」的名作,其人性的光輝與溫柔,幾乎令人忘記冷戰。看DVD所附訪問,美國記者幾乎恨得牙癢癢,不斷追問兩名年輕演員在排練及演出時有無自由、有無個人獨立性;又問導演丘赫萊依(Grigori Chukhrai)如何看自己與其他蘇聯導演的分別,言下之意,為什麼你不像其他人一樣硬崩崩。誰知導演好功夫,一下祭出托爾斯泰、杜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艾森斯坦,說我們俄國有好傳統,全都為我所用,我們個個都不一樣。
好了,那到底是一部怎樣的神劇?背景是二次大戰,一名蘇聯小兵混亂中擊毁了兩輛敵軍的坦克,得到長官的嘉許,但他寧可換兩天休假,好回家替母親修好漏水的屋頂。長官慷慨給他六天,兩天趕回家,兩天趕回軍隊,兩天修屋頂。然後萬水千山,在路途上,他鼓勵不敢回家面對妻子的斷腿士兵;他幫助大辮子少女一同匿藏在裝滿稻草的車卡;他見到戰友日思夜想的妻子早已另有所愛,遂把原本送給他妻子的肥皂轉贈戰友父親。最後在離家十里以外,火車遇上被炸的斷橋,輾轉乘車到達家門,終於得見從田野一路奔跑過來的母親。因為途中的事故,六天的休假至此只剩下一刻,只足夠緊緊擁抱母親一下,小兵馬上又要趕返前線。然而電影開首早已告訴我們,這個小兵戰後沒能歸來,他葬在一個離鄉甚遠的地方,人們在他墳前獻花,說他是一個好兵。電影就是要說他的故事,一個連他母親也不知曉的故事。
左翼美學的極致,原本就是小人物與大時代之對比,硬要搞得個個英雄「高大全」,那是後來的事。十九歲的小兵與辮子女孩一段誠然最動人心魄——他要她記得他,他為她用鐵桶裝水以致趕不上火車,他與她匿藏稻草中的一刻不忘自然地親近她的臉,感受女性的溫暖;她騙他已有未婚夫,她問他男與女可否做純粹的朋友,她不想做純粹的朋友。全電影最美的鏡頭:她髮絲飛動,互相凝視對方的笑靨與年輕正派的臉,一刻不離。然而在顛簸的車廂與樹林月色之間,他們始終未嘗一吻。
小兵之美,全在不計較。能夠欣賞《小兵敘曲》的陳韻文,寫〈有話直說〉也肯定不是為了計較。那為什麼還要寫呢?正正也是因為,能夠欣賞《小兵敘曲》的人,必然明白,藝術的本質,就是表達,講一個好故事。現實裏的無人知曉,是不能動人的,只能是河邊骨、夢裏人。戰爭的餘燼,一點不美。陳韻文提醒我們一切心血與感情皆有來歷,美好事物值得堅持與留痕,我十分同意。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明報》2019年3月25日)
記憶中的事實
陳韻文
2014年一個黃昏,鄧小宇在他家裡介紹我認識影評人曾肇弘。交談沒多久,曾先生突然問我《瘋劫》的一場戲裡,張艾嘉為什麼那樣子吃蛋卷。我因長途跋涉方才著陸,昏頭轉向猶未弄清時差,未及回應,曾先生已經接話:「許鞍華說那是陳韻文吃蛋卷的習慣。」
我登時心醒,記起當年剪片室內,正因坦白說出這場戲以及好幾場戲處理不當,即被許鞍華搶白。
勞師動眾花錢去拍場戲詮釋個茄喱啡編劇吃蛋卷。真不可思議!那場戲是張艾嘉得悉趙雅芝被殺的惡耗,忐忑不安,不知該如何向趙雅芝的祖母說。當年在我家邊寫邊向飯桌另一端的許鞍華解說我下一場寫什麼,口述又同時落墨;寫蛋卷碎紛紛跌落餅乾罐,握刀撩牛油,不意撩個空,失神的張艾嘉無所覺,恍惚瞥見什麼,打個寒噤看前面那度門,見小姪兒自右邊門框緩緩爬出,爬至左邊,未及門框,驀地消失,張艾嘉吃驚看門,不見門外有人,乍覺詭異,正有不祥預感,小姪兒幽幽然自左門爬出,爬向右邊……。
剪片室內,陳韻文就感覺直言;「空鏡停的時間不夠玄 、小孩爬得太快、不見張艾嘉有不祥預感。」那當下只道是有話直說,不知因此結了樑子。陳韻文不識好歹,在下面那場戲又直腸直肚,終被搶白。
趙雅芝祖母在樓頭上困愁呆坐,聞樓頭下那自嗓門扯出心中鬱結的市聲──衣裳竹。雙目失明的祖母聞聲黯然懷想往昔。而樓頭下,張艾嘉正好與肩托大綑衣裳竹的漢子擦身而過。我記得寫這場戲之時,對著許鞍華嘶聲長喊衣裳竹,喊剷刀磨鉸剪。也同時提醒,別讓那漢子露面,漢子的身段以及他肩膊上那排竹倒可以隨着嘶喊而微轉。張艾嘉聞聲轉頭,但見他隻手抓住綑竹粗繩扶住竹,布衣下的身軀以及長褲腿幽靈似的緩轉緩移。可是剪片室內我見漢子在轉身的剎那露了臉,轉身過快。其時我想問又想建議:設若漢子轉身那一下慢半格慢半拍,會是什麼效果。可我方才開腔,幾乎話未完,許鞍華狠狠搶白:「妳識睇毛片咩。唔係咁多人識睇毛片𠺢。」我由是噤聲。由得漢子露面轉身。
最氣悶是挪用家祖母的皮箱,讓她作為伴隨趙雅芝祖母進庵堂的道具。寫那兩場戲之時,我說且當那箱子曾經陪嫁,跟趙雅芝祖母經歴一生滄桑,親人盡去,最後連相依為命的孫女兒也走了,剩下那皮箱隨著她老人家進庵堂。我提醒,可藉那箱子連貫親情,有連戲作用。我沒多說,以為這一點應有共識,因知只要對電影稍有認識,都曉得道具有其語言,有話表達,可反映心理背㬌,也有其歷史背景。然而事與願違,鏡頭前,納進箱内的衣物以及那扛著的箱子轉瞬即過,不覺當中含有沉重感情。剪片室內,看到這一場戲我雖為這箱子叫屈,可又另有所悟,衝口而出說這故事該由祖母扯缐,是祖母有意無意的一兩句提點,促使本性疑神疑鬼的張艾嘉抽絲剝繭牽出案情。喃喃說將來有機會要把《瘋刼》寫成小說。沒料到又被搶白:「妳以為《瘋刼》好咩,值得寫小說咩。」
後來她卻在接受訪問時說:「……《瘋刼》的故事橋段是我想出來的……我知道龍虎山以前曾發生過一宗謀殺案……」我登時見那日下午在我家,我們左翻報右翻報,翻著一頁紙上一幅新聞照,赫然見上半頁一張似今日mini iPad 尺寸的照片,當眼的大石上刻著幾行字,似打油詩,提到男女雙屍,提到蝴蝶。讀著讀著我靈感徐至。許鞍華和胡樹儒等人對傳媒提到《瘋刼》,總說是將龍虎山的雙屍案改編為電影。可我一再申明,電影中人物故事與命案中人物絕不相同,一再提醒應該尊重死者以及其親人,所以宣傳時最好講:「瘋刼乃自龍虎山命案得靈感。」
許鞍華在以前的訪問中曾經提到:構思素材之時,我們的大前提是先向得獎方面設想。是麼?這個「我們」若有陳韻文在內,大錯特錯。
《桃姐》編劇陳淑賢得獎。我忍不住說:「Ann,若果同佢合得來,咪換來換去,次次重新適應。好辛苦。」她沒有回應,可未幾莫名其妙來一句:「我唔可以提妳。我要俾面我嘅編劇。」什麼意思呢?以為我那番話是以退為進想跟她攞個獎?我當下回道:「妳太唔認識我。妳都唔知我嘅價值觀係乜。」
2017年的訪問中,她一再提到邱剛健改寫陳韻文的劇本。我絕不奇怪。知她早已認定「投奔怒海」是我的軟肋。還說呢:「陳韻文也沒有因為這件事而生氣。我覺得她自己也認為改得好。」
陳韻文沒認為改得不好,也沒認為改得好。陳韻文更沒有請許鞍華做「代言人」。我至今未看過「投奔怒海」。至於劇本,那年那日關錦鵬帶劇本來我家,也帶感冒進門來。而我平生最怕感冒。本意為看看邱的劇本中可有我寫的幾場戲。特別是第一場:「馬斯晨飾演的琴娘蹲在路旁賣粿條。她的小弟為幫家裡賺個零碎錢而被哄做人肉炸彈,擦身經過馬斯晨,開開心心放下錢,奔向美國大兵,當馬斯晨有所警覺,已來不及叫住,瞬刻見小弟不慎跌步,被炸死。有人順手扯過插在一旁的國旗,蓋到孩子身上。血自國旗下滲染,滲化開來的血印如越南地圖,此際,字幕亦徐徐上。」我匆匆翻閱,不見這開場,不見我心悅的幾場戲。鬆口氣遣走患感冒的關錦鵬。本來想請他帶本書去給邱剛健參攷,轉念間想到可給許鞍華,轉念間又把書放下。那是著名的意大利女記者 ORIANA FALLACI 的 Interview With Histry。
FALLACI是我景仰的女記者。真有才華,觸角敏銳,性情真摯,既瀟洒又細心。戰地上病榻上都那麼硬朗那麼乾淨俐落。難得的是,周旋於各國政要中,始終保持平衡。她在字裡行間帶出被訪者性格,也預示他們對將來世局的看法,取捨而至所採取態度。她與被訪者討論原則性問題,可也 不忘自己原則。FALLACI 之所以髙貴,因為她絕不為五斗米折腰。這書中,她訪問北越的武元甲,南越的阮文紹。今日回想,當年當日縱然不借書給邱剛健,應該借給許鞍華。讓她看清原則,看如何把持自己,學一點平衡工夫。可是當我知道「明月幾時有」為什麼找葉德嫺,為什麼淪陷時期無原無故出現黃傘。當友人向我分析,為什麼這電影左右逢源。我由是瞭然。我懷念早逝的 FALLACI。
(原刊香港《蘋果日報》2019年3月16日。此為第二稿,見陳韻文臉書2019年3月17日。)
有話直說
陳韻文
「…跟陳韻文合作,通常都是我先講故事,講清楚我想怎樣拍,找齊資料跟她討論,你一句我一句,因為她沒時間,只負責把劇本寫出來,另外有些劇本已經寫好了,但她覺得不妥,於是突然刪去一半,並由中間開始再寫…」
很想知道,我幫許鞍華寫的三個電影劇本,哪一個是由她先講故事。
「投奔怒海」,最先是梁普智和我跟著傳道團體進啟德難民營;趁人家傳道,我們分頭在隱蔽遠角問難民在越南之辛酸以及海途中險惡;幾次之後我們的身份被識破,被禁足。幸而從難民口述的經歷、從時事新聞與報刊記載,所得資料十分充足。我又找到一日本記者敘述兵慌馬亂中所見的越南人種種際遇。我因此建議由一日本記者牽引故事。當時一則哄動的新聞乍令梁普智野心勃勃,要拍攝難民船漂泊至印尼,聯合國這回安排難民上岸,印尼人迅即放火燒船,不讓蛇頭駛船返越南贃銀。梁普智因而想到在火光熊熊的畫面上打出「劇終」二字。就因為這構思,他這部電影被嘉禾何冠昌喊停。若干時日後,嚴浩與我斟酌劇本,可未幾因顧及台灣反應而改變主意,交棒給許鞍華,由我講故事。也由我向夏夢和新華社的王匡交代大綱。所以問,陳韻文兩隻耳朵,哪一隻聽過許鞍華講「投奔怒海」的故事。
陳韻文倒記得「投奔怒海」劇本的第一稿是連開兩晚通宵寫成。寫一場交一場給許鞍華,也不只一次提醒她,不管好壞都千萬別撕掉。因記「瘋刼」有一塲戲,寫張艾嘉交驗孕收條給醫務所,拿報告;護士的白眼令她明白趙雅芝所受壓力,因而同情趙雅芝。許鞍華匆匆一讀之後說不須要這場戲,把稿紙撕掉。戲煞青後卻突然問:「若果保留那場戲會否更好。」
「投奔怒海」第一稿是在第二個通宵的早晨七時光景完成。許鞍華挾劇本去夏夢的公司「青鳥」,趕赴製作會議。出門時大聲大氣說:「妳個劇本好吖。呢次唔會有人話妳劇本唔好。」而我提醒這是第一稿,未盡滿意。第二稿再說吧。之前,専欄中我不只一次提到「瘋刼」曾經小改十六次,大改則有七次之多。正因為我記得這些數字,以及無數次自動自發的刪刪改改,我很受不了後來與她相遇時,被她在十多人跟前揚聲搶白的一句話:「乜妳咁怕人話妳要改劇本。妳劇本唔好就要改。」又正因為那早晨七時才岔開她讚劇本的話,因方才表示寫了第二稿再說,豈料兩個鐘點後,她竟然來電話,劈頭說:「喂妳劇本唔好呀。攝影話你劇本唔好,美指話妳劇本唔好,製片話妳劇本唔好,副導演話妳劇本唔好。」
訪問中,許鞍華將她當日在電話中轟我的話重轟一次。說到邱剛健改我的劇本,更安插這麼一句「…不過邱剛健就像陳韻文刪了別人一半的劇本一様,刪掉了陳韻文寫的一半內容…」
我沒有改過許鞍華交來的「別人」的劇本。若果她指的是張堅庭的「胡越的故事」,我可是記得清楚;一個早上,她請我去假日酒店地窖的Delicatessen 早膳。拿著張堅庭的劇本要我看,叫我幫忙改。我只管喫,始終沒碰過劇本一下。由得她自說自話。到最後,她急了,頓足問:「妳咁都唔肯幫我!」我抹抹嘴,說:「Ann,言猶在耳,記唔記得妳同我講過:我係要搵妳寫劇本嘅咩?我唔搵妳,妳吹吖!」
陳韻文與張堅庭年來仍有聯絡。陳韻文到今天未讀過「胡越的故事」,更別說刪去半個劇本。
許鞍華那句話指的不可能是「桃姐」、「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更不可能是2017年,她接受訪談期間傳來,叫我幫她審視的第四個唔知乜水寫的劇本。
「桃姐」我看罷告訴她,這劇本若改為黑色喜劇可以突出,沒那麼老土。她說不行,葉德孄和劉德華都不會喜歡,不會演。結果給她磨著寫了六塲戲。只是加寫,我沒刪。她有否刪則不得而知。後來她問我可有看到我寫的第一塲。我暗喊死火。我認不得,即是她拍得三不像。幸而還有幾塲戲猶可識辨。然後,她突然來短語:「我唔可以提妳,我要俾面我嘅編劇。」我回道:「妳太不認識我。妳都唔知我嘅價値觀係乜。」
我更不可能刪掉一半「黃金時代」。她千叮囑萬叮囑,千萬別讓李檣知道我看過他的劇本。我力陳劇本不是之處,她做個様逐點筆記。可我知道她沒改。因為電影在威尼斯影展上映一塲之後,她的摯友當即傳來Hollywood Reporter和Variety 兩大影評。文中所指「黃金時代」的缺點,point to point 正是我告訴她劇本的弊病。
然後,突然一天,她來言問可有空幫眼看她的新劇本。記得我回說:即使我指出不是之處妳又不改掉,哪問來幹嘛。她說呢:「妳都唔想我聽晒妳話㗎。」之後,傳來「明月幾時有」。我看罷狠狠的質問了許多問題,卻一句該如何攺動的話都沒說。更別說動手刪去人家一半劇本了。至於她在2017年交給我的第四個劇本。我壓根兒沒向她哼一聲。她差摯友來打聽。我只回那人一個字。就一個字。
好啦。說至此,暫時打住。
下星期六再續。當然要再續。因為得釐清其他電視電影劇本的來源,那幾部不是許鞍華的故事。都有得好說。她把我的劇本拍壞了哪幾點,也不妨一吐為快。又,訪問中她有好些關於我的話甚多疑㸃,既說得前言不對後語,亦與現實不符,可以說是生安白造,屈得就屈。而我是不甘受屈的。
(此文原刊香港《蘋果日報》2019年3月10日,本網刊出的是作者的第二稿,畧有增補。)
(按︰文中提及的許鞍華訪問見《許鞍華‧電影四十》,頁160-185,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1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