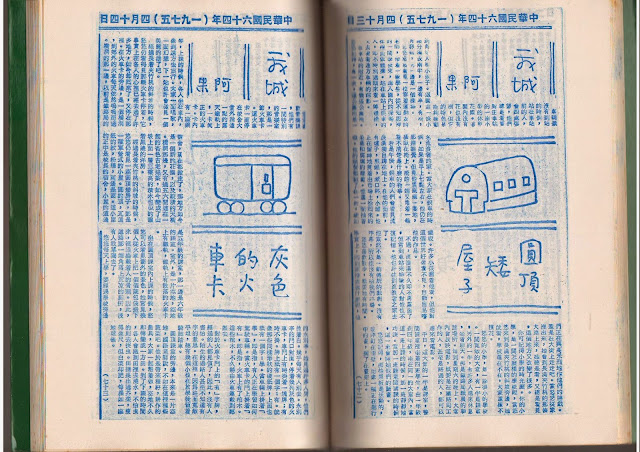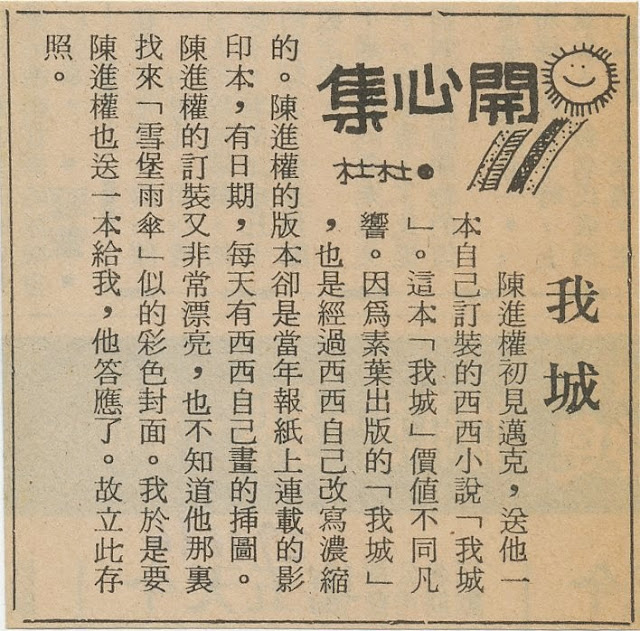《坐井集》
胡菊人(一九三三~)一九五五年走進香港文化界,加入友聯出版社工作後,先後曾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今日世界》、《明報月刊》、《中報》、《中報月刊》、《百姓》……等報刊的編輯及社長等職。不單負責編輯工作,還要寫大量文稿,但他出版的著述卻不多,只有《旅遊閑筆》、《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文學的視野》和《小說技巧》等幾種。如今大家見到的《坐井集》(香港正文出版社,一九六八),是他的第一部單行本。封面是文樓的絲版畫,封面與封底通版,這位枕手半躺的「坐井者」,是冷眼觀天還是思考人生不同際遇?
《坐井集》是四十開本的袋裝書,一七二頁,約十萬字,收雜文五十一篇,大多屬讀書筆記類,以談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的為主,差不多全是當年《星島晚報‧文化周刊》中《坐井集》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馬場贏來的稿費》,寫某詩人在馬場贏了錢,回家交給母親時,卻說是「賣了一部劇本」的收入,企圖改變母親認為「作家必窮死一世」的觀念。可悲!
《坐井集》一九六八年初版一千七百本,一九七O年再版,我的這冊是一九七二年的三版。胡菊人在《再版序》中說,此書在當年來說,已是值得一再提及的文學暢銷書,但比起武俠小說和「老夫子」卻望塵未及。無奈!誰叫你選擇了文學?
《大公報》文藝獎
為了鼓勵創作,《大公報》在一九三六年舉辦了「文藝獎金」盛事,得獎的作品:戲劇獎是曹禺的《日出》,小說獎是蘆焚的《谷》和散文獎何其芳的《畫夢錄》。此事於一九三七年公佈,但因是年展開「七七抗戰」,以後十多年,整個中國陷入紛亂的局面,得獎金之事雖是文壇大事,但與瞬息萬變的國事比,不過是小事一宗,事後誤傳不少。
上世紀中葉的一九五O至七O年代,玄默、陳紀瀅、劉心皇、司馬長風……等人均提過《大公報》「文藝獎金」的事,但有關得獎的人和作品多有謬誤,甚至有人增加了一項孫毓棠《寶馬》得詩歌獎的事。後來劉以鬯先生經多番聯繫,搜尋資料,在一九七八年寫了〈《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收《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1982),證實了上述三位得獎者及作品的正確性。
今日翻靳以編的大型純文藝月刊《文叢》,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第一卷四號,刊內有佔整頁「當選大公報二十五年度文藝獎金之三大傑作」的揭䁱消息,還刊出這三部作品的得獎原因。出版了數十年的戰時期刊《文叢》當然不易找,但,首四期一九七O年代香港有重印本,如果他們多翻書,找到這頁消息,即可證據確鑿,不會發生論戰了!
《範菴雜文》
潘範菴是活躍於一九三O年代香港的文化人,他一九二九至三三年在香港《大光報》編文藝副刊,同時以筆名「老範」闢《飯吾蔬菴》寫雜文專欄,後因病辭職,轉到培正中學教書。當時的教材一般多由老師自行決定,潘範菴便從自己所寫的雜文中選些適合的供學生閱讀,後來索性把文章編成《範菴雜文》於一九三八年出版,如今大家見到的,則是一九五四年香港大眾書局的增訂版。
《範菴雜文》內的文章多寫於「九一八」之後,「七七」全面抗戰的大風暴前夕,內容多是積極而具戰鬥意義的,換句「老範」自己的話,那是箍動大石頭投到大海裡,引起浪湧的雄邁行動,尤其〈解除國難的「花選」〉、〈日軍攻察哈爾問題〉、〈為甚麼要紀念屈原〉、〈黃花節痛言〉……等篇,極具時政價值。作為本書代序,陳君葆給潘範菴的信中,即盛讚書中的文章是「有血有肉的東西,充滿着奔迸的血和淚的作品」,還說他的文章受魯迅的影響很大,很有諷刺性。
潘範菴雖是新舊文學的過渡人物,舊文學基礎不弱,間中寫舊體詩文,但也寫新小說,《範菴雜文》過百篇雜文中,即有新詩〈心的哀弦〉和〈兩個撒馬利亞人〉、〈老槍的哲學〉等小說創作,可惜寫的不多。
今聖嘆的回想錄
一九七O年代後期,有一間開在九龍高級住宅區又一村達之路上,叫「文化‧生活」的出版社,出過一批以名人掛帥的文學書,記憶中有曹禺、老舍等《北京的回憶》、《黃霑隨筆》、胡金銓的《老舍和他的作品》、今聖嘆的《新文學家回想錄》和董橋的《雙城雜筆》。
寫《新文學家回想錄》(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的今聖嘆,原名程綏楚,卻以字程靖宇名於香港文壇。他是成長於北平的湖南衡陽人,戰時畢業於西南聯大史學系,為陳衡哲及陳寅恪入室弟子,並甚得胡適器重,曾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一九五O年移居香港,以教學及寫作為業。胡適逝世後,曾編《胡適博士紀念集刊》(香港獨立論壇社,一九六二) 單行本。
近十一萬字的《新文學家回想錄》,收談人物的雜文三十餘篇,所涉人物周作人、馮友蘭、趙元任、劉文典……等均為民國學術界名人,難得的是今聖嘆過去曾與他們交往過,資料翔實以外,他行文語帶輕鬆幽默,讀之趣味盎然,如〈趙元任函授習游泳〉、〈吳雨僧痴情毛彥文〉、〈廢名打坐兼打架〉、〈詩人最多「未亡人」〉、〈顧一樵博學多情〉……等,單看題目已知秘聞味甚濃,甚受歡迎!此外,〈記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陳衡哲〉和記胡適的〈不廢江河萬古流〉,更因體驗較深,下筆兼及師生情誼,推為本書首選,不可不讀!
新雷詩壇
一九五五年八月,香港一群愛寫新詩的朋友:林仁超、吳灞陵、佘雪曼、黃宇乾、趙滋蕃、慕容羽軍、袁家松、袁效良……等成立了「新雷詩壇」,樹起鮮明的旗幟,廣播自由詩的種子,聯繫志同道合的詩友,共同為新詩的前途而努力。他們確定了「寫詩八要」,主張:要流露情感、要用白話抒寫、要音節協調、要用諧音押韻、要不拘句數、要忠於現實、要不避粗俗事物的描寫、要注意修辭。
「新雷詩壇」的主要人物是林仁超(1914~1993),他一九五O年代曾主編《漢山雜誌》,發起組織「新雷詩壇」外,還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同名雜誌,一年後出版詩論與詩章合集《新雷集》(香港新雷詩壇,一九五六)。此書為三十二開本,九十九頁,前邊收吳灞陵及林仁超的詩論〈新詩的欣賞〉、〈新詩的道路〉、〈新雷詩壇的作風〉……等五篇,主要在闡明他們的「寫詩八要」,及叙述「新雷詩壇」成立的經過;後半部收詩友的創作四十多首:〈永恆的琴音〉、〈百合花〉、〈水之湄〉、〈春天去後〉、〈孤星〉、〈夜香港〉、〈詩人與海〉……主要是抒發內心情緒之作。
以今天的標準衡量,《新雷集》中的作品當然是淺白的,欠成熟的,但這是本地新詩拓荒者走過的路,亦足一記。
胡菊人(一九三三~)一九五五年走進香港文化界,加入友聯出版社工作後,先後曾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今日世界》、《明報月刊》、《中報》、《中報月刊》、《百姓》……等報刊的編輯及社長等職。不單負責編輯工作,還要寫大量文稿,但他出版的著述卻不多,只有《旅遊閑筆》、《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文學的視野》和《小說技巧》等幾種。如今大家見到的《坐井集》(香港正文出版社,一九六八),是他的第一部單行本。封面是文樓的絲版畫,封面與封底通版,這位枕手半躺的「坐井者」,是冷眼觀天還是思考人生不同際遇?
《坐井集》是四十開本的袋裝書,一七二頁,約十萬字,收雜文五十一篇,大多屬讀書筆記類,以談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的為主,差不多全是當年《星島晚報‧文化周刊》中《坐井集》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馬場贏來的稿費》,寫某詩人在馬場贏了錢,回家交給母親時,卻說是「賣了一部劇本」的收入,企圖改變母親認為「作家必窮死一世」的觀念。可悲!
《坐井集》一九六八年初版一千七百本,一九七O年再版,我的這冊是一九七二年的三版。胡菊人在《再版序》中說,此書在當年來說,已是值得一再提及的文學暢銷書,但比起武俠小說和「老夫子」卻望塵未及。無奈!誰叫你選擇了文學?
《大公報》文藝獎
為了鼓勵創作,《大公報》在一九三六年舉辦了「文藝獎金」盛事,得獎的作品:戲劇獎是曹禺的《日出》,小說獎是蘆焚的《谷》和散文獎何其芳的《畫夢錄》。此事於一九三七年公佈,但因是年展開「七七抗戰」,以後十多年,整個中國陷入紛亂的局面,得獎金之事雖是文壇大事,但與瞬息萬變的國事比,不過是小事一宗,事後誤傳不少。
上世紀中葉的一九五O至七O年代,玄默、陳紀瀅、劉心皇、司馬長風……等人均提過《大公報》「文藝獎金」的事,但有關得獎的人和作品多有謬誤,甚至有人增加了一項孫毓棠《寶馬》得詩歌獎的事。後來劉以鬯先生經多番聯繫,搜尋資料,在一九七八年寫了〈《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收《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1982),證實了上述三位得獎者及作品的正確性。
今日翻靳以編的大型純文藝月刊《文叢》,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第一卷四號,刊內有佔整頁「當選大公報二十五年度文藝獎金之三大傑作」的揭䁱消息,還刊出這三部作品的得獎原因。出版了數十年的戰時期刊《文叢》當然不易找,但,首四期一九七O年代香港有重印本,如果他們多翻書,找到這頁消息,即可證據確鑿,不會發生論戰了!
《範菴雜文》
潘範菴是活躍於一九三O年代香港的文化人,他一九二九至三三年在香港《大光報》編文藝副刊,同時以筆名「老範」闢《飯吾蔬菴》寫雜文專欄,後因病辭職,轉到培正中學教書。當時的教材一般多由老師自行決定,潘範菴便從自己所寫的雜文中選些適合的供學生閱讀,後來索性把文章編成《範菴雜文》於一九三八年出版,如今大家見到的,則是一九五四年香港大眾書局的增訂版。
《範菴雜文》內的文章多寫於「九一八」之後,「七七」全面抗戰的大風暴前夕,內容多是積極而具戰鬥意義的,換句「老範」自己的話,那是箍動大石頭投到大海裡,引起浪湧的雄邁行動,尤其〈解除國難的「花選」〉、〈日軍攻察哈爾問題〉、〈為甚麼要紀念屈原〉、〈黃花節痛言〉……等篇,極具時政價值。作為本書代序,陳君葆給潘範菴的信中,即盛讚書中的文章是「有血有肉的東西,充滿着奔迸的血和淚的作品」,還說他的文章受魯迅的影響很大,很有諷刺性。
潘範菴雖是新舊文學的過渡人物,舊文學基礎不弱,間中寫舊體詩文,但也寫新小說,《範菴雜文》過百篇雜文中,即有新詩〈心的哀弦〉和〈兩個撒馬利亞人〉、〈老槍的哲學〉等小說創作,可惜寫的不多。
今聖嘆的回想錄
一九七O年代後期,有一間開在九龍高級住宅區又一村達之路上,叫「文化‧生活」的出版社,出過一批以名人掛帥的文學書,記憶中有曹禺、老舍等《北京的回憶》、《黃霑隨筆》、胡金銓的《老舍和他的作品》、今聖嘆的《新文學家回想錄》和董橋的《雙城雜筆》。
寫《新文學家回想錄》(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的今聖嘆,原名程綏楚,卻以字程靖宇名於香港文壇。他是成長於北平的湖南衡陽人,戰時畢業於西南聯大史學系,為陳衡哲及陳寅恪入室弟子,並甚得胡適器重,曾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一九五O年移居香港,以教學及寫作為業。胡適逝世後,曾編《胡適博士紀念集刊》(香港獨立論壇社,一九六二) 單行本。
近十一萬字的《新文學家回想錄》,收談人物的雜文三十餘篇,所涉人物周作人、馮友蘭、趙元任、劉文典……等均為民國學術界名人,難得的是今聖嘆過去曾與他們交往過,資料翔實以外,他行文語帶輕鬆幽默,讀之趣味盎然,如〈趙元任函授習游泳〉、〈吳雨僧痴情毛彥文〉、〈廢名打坐兼打架〉、〈詩人最多「未亡人」〉、〈顧一樵博學多情〉……等,單看題目已知秘聞味甚濃,甚受歡迎!此外,〈記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陳衡哲〉和記胡適的〈不廢江河萬古流〉,更因體驗較深,下筆兼及師生情誼,推為本書首選,不可不讀!
新雷詩壇
一九五五年八月,香港一群愛寫新詩的朋友:林仁超、吳灞陵、佘雪曼、黃宇乾、趙滋蕃、慕容羽軍、袁家松、袁效良……等成立了「新雷詩壇」,樹起鮮明的旗幟,廣播自由詩的種子,聯繫志同道合的詩友,共同為新詩的前途而努力。他們確定了「寫詩八要」,主張:要流露情感、要用白話抒寫、要音節協調、要用諧音押韻、要不拘句數、要忠於現實、要不避粗俗事物的描寫、要注意修辭。
「新雷詩壇」的主要人物是林仁超(1914~1993),他一九五O年代曾主編《漢山雜誌》,發起組織「新雷詩壇」外,還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同名雜誌,一年後出版詩論與詩章合集《新雷集》(香港新雷詩壇,一九五六)。此書為三十二開本,九十九頁,前邊收吳灞陵及林仁超的詩論〈新詩的欣賞〉、〈新詩的道路〉、〈新雷詩壇的作風〉……等五篇,主要在闡明他們的「寫詩八要」,及叙述「新雷詩壇」成立的經過;後半部收詩友的創作四十多首:〈永恆的琴音〉、〈百合花〉、〈水之湄〉、〈春天去後〉、〈孤星〉、〈夜香港〉、〈詩人與海〉……主要是抒發內心情緒之作。
以今天的標準衡量,《新雷集》中的作品當然是淺白的,欠成熟的,但這是本地新詩拓荒者走過的路,亦足一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