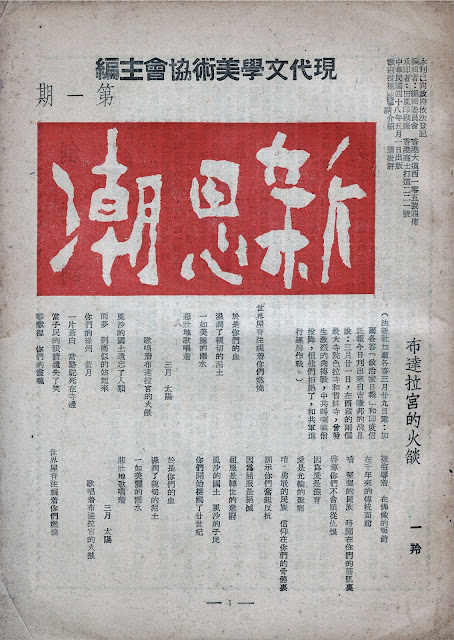關於綠雲的通信
【馬吉按:詩人羈魂(胡國賢)跟插畫家綠雲之子張鴻堅原是中學時好友,他最近在臉書看見有人談綠雲,遂向張鴻堅問詢,蒙其俯允,回函提供其父不少資料,彌足珍貴。感謝羈魂將函件轉交本網站發表。】
國賢兄:
家父已於2003年去世 ,時值「沙士」之年, 一度被醫生懷疑為「沙士」肺炎, 最後以普通肺炎離世,終年九十歲(1913-2003)。
父親是一個畫家,最初在廣州市立美術學校修讀西洋畫,其後師從國畫大師鍾若冰學習國畫。工作方面一向都在報館工作,曾担當不同崗位,最後以繣畫插圖為其終生職業。他以自由身的身份工作,並不隸屬任何一位顧主,因此他的自我介紹說自己「是走卒、也是統帥」。他的工作量最多的報館是《成報》,其他的還有《商報》、《華僑日報》、《明燈日報》、《紅綠日報》等等。由於他不用上班工作, 他的睡房也是他的工作間;對他的孩子來說,這是一位很特別的父親,因為他整天都在家裏,卻又任何時間都在工作,沒有星期日、也沒有公眾假期,全年休息的日子就只有報紙不出版的日子(那就是農曆新年),報紙年初一不出版,父親就在年卅晚不用工作。在我的回憶裏,父親每一年只有一天會回到報館去,那就是九月一号的「記者節」晚宴,我們總是期望這一天,因為父親總是會帶一份名貴的抽獎禮物回來,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父親對所有人都很好,也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他沒有很多嗜好,只喜歡繣畫和看書。他的書法很美,中文根底很深;他不諳英語,奇怪是他不看中文電影,只看西片;而他訂閱的是英文Geography Magazine,因為裏面有許多有趣的圖片。由於父親總是在工作,他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就主要是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他總不忘記說一些做人道理,每一天都聽,漸嶃也沒有新意了,然而孩子們就是這樣成長起來。
他有一女四子。大女兒生於戰前(1938),四個小子全部生於戰後(1946,1948,1950,1952)。父親就是在大戰期間帶同太太和女兒從廣州逃到香港,其實在大戰期間也還生了一個兒子,可惜戰時衛生環境不好,最後因腸熱病死了。
父親在吃飯時也喜歡說故事。以下就是他說的兩個他戰時親身經歷的故事:
故事一:在香港的日治時期,父親在華僑日報工作,但他暗暗從事間諜活動,利用報紙的版頭圖片設計作為間碟行動的暗號。最後引起日本人的懷疑,把父親召到軍部問話,幸而因證據不足,日本人把父親釋放,父親也不敢再用這種方式傳送訉息了。
故事二:在香港的日治時期,生活艱苦。有一天有人遺下一大堆米包在街上,一群青年人擁上前去搶米,父親身體瘦弱被人推到後面,唯有自嘲「百無一用是書生」。話還沒説完一隊日本兵巡至,馬上開鎗把前面的青年人擊斃。父親說這故事時就説:「如果我身體強壯搶得到米,你們這四隻馬骝也不會來得人世了。」
父親從沒有開過個人畫展,只有一次和鍾若冰老師開過一次師生作品展。他在《商報》有一個「地盤」是一幅漫畫加一首打油詩,在1997年他就申請了藝術發展局的資助把這漫畫打油詩結輯成集,就是你的電郵引述的「作者簡介」的出處, 其中數句:「少有志,老無成,渾噩半生,晚有所悟」道盡生平,最為人津津樂道。1997年後他的頭腦開始不靈活,背也漸漸向前彎。至於他遺下的畫作,大部份藏於在澳門的一個外甥女那裏。
至於我自己,我覺得很遺憾並沒有收藏父親的遺作,也沒有什麽其他現成的資料可以提供給你的朋友。不過如果他需要進一步的資料,他可以寫信給我四弟張鴻剛,因為他仍在父親的故居居住,裏面可能仍有關於父親的資料和遺物。他的通信地址是:
九龍油蔴地渡船角……
倘若你的朋友將來有什麽關於我父親的著作,我將會有興趣閱覽。祝安康!
張鴻堅
插畫家綠雲
Linda Pun:五、六十年代香港著名插畫及漫畫家綠雲在1997年出版詩畫冊《浮世吟繪》,在最後一頁的作者介紹。黃仲鳴2006年8月6日在文匯報發表的文章〈插圖家綠雲小記〉如是說──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一些報紙副刊上,常見兩位插圖家,一位是雲君,專為金庸、梁羽生的小說添上華衣;另一位就是綠雲,他的畫風較廣,古今皆繪,不少作家的小說,都見他的傑作,如高雄、怡紅生、靈簫生、傑克、俊人、望雲、任護花、宋玉等。後來,雲君移民外國,「香江兩雲」只剩下一「雲」。綠雲最後一幅插圖,是林蔭在《香港商報》的連載小說〈瑪莉亞的迷惑〉。
近期整理一些舊報資料,綠雲的插圖一幅幅呈現眼前。這些珍貴的資料,迄無人整理,更無人提起,禁不住使我對圖興嘆。很多年前,我便有此感慨:和一些通俗作家一樣,綠雲的生平資料再無人勾沉,遲早被時間沖刷,了無痕跡。
二OOO年時,我任《作家》雜誌主編,曾囑林蔭往訪綠雲。林蔭不負所託,將老去、舉步維艱的綠雲活生生描繪出來,使我們對他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認識。而在此之前,林蔭也鼓勵綠雲將他的漫畫和打油詩,彙編成《浮世吟繪》一書,讓我們知道,除了為作家「作嫁」外,他還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
但,那些插圖,尤其是他的工筆繡繪出來的插圖,我覺得一樣寶貴,值得搜羅出來,編成一本《綠雲插畫集》,俾流傳永遠。
綠雲接受林蔭訪問時,年已八十七歲,行動不便。回歸那年八十四歲,他編輯《浮世吟繪》,步履仍爽健,想不到僅僅三年,便衰弱若斯。近日致電林蔭,詢問他的近況時,林蔭說很久沒和他聯絡了。我立即叫他致電問候。草此文時,始悉他已於二OO三年三月去世,享年九十歲。他的死訊,文化界竟無人知曉。一個服務報界凡六十餘年,生時是炙手可熱的畫家,死時卻寂寂,寧不令人扼腕?
「綠雲」是他的號,也是他的筆名,原名張艾,生於一九一三年,廣東番禺人,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曾任《華僑日報》副刊「僑樂版」編輯。他第一幅插圖是怡紅生的小說。
他在《浮世吟繪》中曾自嘆:「少有志,老無成,渾噩半生,晚有所悟,這正是『回首向來蕭瑟處……一簑煙雨任平生。』」如斯「渾噩」的話,綠雲太自謙了。
綠雲不僅是畫家,還寫過小說、散文、詩詞。他的打油詩,不僅俗,也雅,非一般粗俗作品可比,如《浮世吟繪》中的〈弄蛇者〉:
「誰趁蛇年去弄蛇,蛇頭岳起哨開牙。人心不足蛇吞象,笛嘴吹來鳳變鴉。最怕一時玩出火,做成兩代大冤家。世情已悉如春夢,何必勞神自作枷。」
七十七歲時,曾作〈自壽〉詩:
「步入七十七,情操定於一;尚有新思潮,漸無舊傲骨。樂觀青海水,喜用白描筆。彷彿遇故人,悠然過今日;豈云憂難忘,慷慨不可失。」
洞悉世情如春夢,至老仍接受新思潮,綠雲確是一人物。
Thomas Wong:不知生死,融入浮世吟繪。
Awong Honsan:張前輩插圖能古能今,詩詞能莊能諧,奇才也。晚年打油詩見於松柏之聲,音韻鏗鏘,意境深遠,佳作數之不䀆。
Awong Honsan:綠雲古裝插圖極具繡像美,時裝人物,妙在男角以張活游為藍本,女角迫肖白燕。
Linda Pun:
Awong Honsan:綠雲不重視他的工筆小說插圖,十分可惜!
Linda Pun:不重視是指他畫得很馬虎嗎?
Awong Honsan:畫家未必真正了解自己作品的優劣,也許他認為依附人家小說作圖不夠痛快吧,其實他每插圖都是精品,與他同期的插圖畫家亦然,而且各具風采,如今全部煙滅,真是一大憾事。
Linda Pun:還可在舊報章中尋回,只是沒有人整理。
(
Linda Pun臉書二O一六年七月一日)
陸文英、陳荊鴻、陳桂權、張艾的粵語詩
方寬烈
陸文英原籍廣東南海,抗戰前在廣州共和報當編輯,又辦時事通訊社,任社長。能詩文,擅辭令,被稱為廣州報界八大仙之一。有一回因兩位老友為詩句爭論,他居中做和事佬,事後戲用廣州話寫一首律詩,也相當妙:
「兩老猶似細佬哥,一時高興撚哩囉,忽然頂頸呼勾臭,累到知心去拍和。既是無恭何用谷?不妨有屎大家屙,千古奇聞詩作怪,論交應及海鹹河。」
廣州淪陷後陸文英居香港,在麗澤女子中學任中文教師,一九六九年去世,著有《陸文英先生詩》。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廖恩燾在香港逝世,他的好友詩人書法家陳荊鴻,依廖的八十四歲自壽詩體,作一首粵語詩追悼他:
「壽桃食過幾多勻,百歲牌坊叫得聞,嬉笑吟來興粵語,外交派去講番文。老婆誇口唔纏腳,國事擔心懶濕身。有乜睇頭班咁戲,不如拍手就鬆人。」
寫得不錯,尤其是「拍手鬆人」形容得妙,不過因為用俚語,沒有收入陳所著的《蘊廬吟草》裏面。
最近友人林蔭兄,轉贈一冊張艾所著的《浮世吟繪》,張艾筆名「綠雲」,是香港著名的小說插圖家,本書出版的時候,他已八十四歲了。退休在家。料不到他既能畫又能詩,詩句淺白可誦,畫裏每一幀畫賦詩一首,切題切意,各有佳處。試摘錄幾首用廣東俗語所寫的詩:
計劃
計仔多多咪當真,度來度去發炆嗔,通書一部睇唔老,岔路多條最壞神。勒住個蘿來吊頸,稔埋脫殼免傷身,雖然未算蠶蟲計,仍怕隨時會累人。
唔岔老
真鬚刮去換磁牙,僥倖而今眼未花,腰骨看真仲冇直,腳頭一假只能爬。唔同小子爭成果,尚有閒心去飲茶,幾十歲人抬慣亭,故將死蟹當生蝦。
炒外幣
猶記當年一千七,人人面孔如來佛,今炒外幣亦相同,早晚行情吼到實。斬吓眼睛撈粗野,岳高頭殼賺幾筆,明朝風險將如何,未便大聲喊得失。
這首詩用仄聲押韵,比較特別。「一千七」指當年恒生指數由七百點升到千七點,炒股票者皆大歡喜,面露笑容。
(節錄自方寬烈〈談廣東方言的格律詩〉,刊
《粵語文化傳播協會》網頁)
打油郎張艾
《松柏之聲》的讀者,對打油郎所寫的專欄,一定不會感到陌生;他寫的詩風趣幽默,早已深入讀者心中。不說不知,打油郎寫詩幾近七十年,是香港報界的老前輩。
打油郎原名張艾。他除了用打油郎作筆名外,最為人熟悉的還是以「綠雲」為名寫詩,在各大報章發表。他的詩大都以社會現況為題材。
他的打油詩讀來風趣抵死,間中夾雜粵語方言,令讀者更能意會詩中神韻。另一方面,他寫的律詩絕句,郤講究平仄對偶,絕不馬虎。其實,張先生除了寫詩外,還為自己的詩劃按圖。他的詩和連環圖,見報率相當高,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他的連環圖故事,有的發行成單行本,有的給拍成電影,當中的「玉面霸王」、「女黑俠」等,都是傳誦一時的佳作。
張艾先生現年八十五歲年青時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十六歲便投身社會,直到一九九一年寫作《告別》一詩,向讀者揮手道別後,便正式退休,過其閒適的生活。
退休後,張先生仍然寫詩繪畫,以作自娛。一九九七他八十四歲那年,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認同及資助,出版了《浮世吟繪》,輯錄了近一百五十首詩與畫。編錄期間,張先生因恙入院,他就在醫院中完成該書的校對工作。他對工作的認真態度,可見一斑。
他年少奮鬥,老年抱定處世謙卑及終生敬友的經歷及抱負,在他八十三歲時所寫的詩中表露無遺,正是張艾先生的寫照,且看:
幾多往事豈能忘,此是平安舊戰場。
勁竹也曾抽苦筍,蒼松依舊傲冰霜。
疾風難折江蓬草,細雨還呵陌上芳。
八十三年無那老,不妨含笑認清狂。
張艾先生(左)繪的畫深受年青人歡迎
(原刊
《松柏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