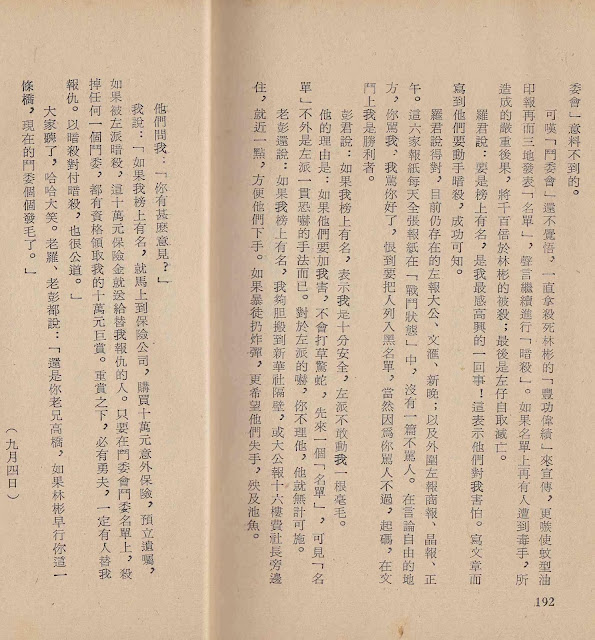鐵漢萬人傑(陳子雋)
Linda Pun
萬人傑五十年代與家人合照
近年中共對香港的制肘和影響越趨嚴重,從政治選舉到購買嬰兒奶粉等日常生活問題,香港人都飽受來自大陸的壓力,以致民怨沸騰,激起新一波的反共思潮。在網上討論區,不時有網友提及香港已故反共報人萬人傑,及把他的精警言論上載分享,可見萬人傑雖已離世二十五年,他的名字依然深深印在不少港人的記憶中。適逢近日萬人傑太太何智明從美國回港探親,筆者專訪何女士及多名昔日萬人協會的會員,並隨他們到萬人傑的墓地致祭,追思這位在六七暴動期間名噪一時的反共健筆。
萬人傑原名陳子雋,廣東番禺人,一九一七年生於廣東。他在十兄弟中排行第五,還有幾位兄弟也在香港從事報業工作,包括六弟子多,為漫畫家,報紙副刊編輯、七弟子龍,曾任職快報編輯主任、九弟子靜,為記者和影評人。一門四傑,成為報壇佳話。
萬人傑的父親三十年代在香港利舞臺任職宣傳畫師,因家貧,萬人傑在廣州廣雅中學初中畢業後便輟學,到香港隨父謀生。一九三三年進《大光報》任校對,那時《大光報》的社長鄭水心對這位勤力聰敏的十六青年十分賞識,提拔他為助理編輯,逐步擔任採訪和編輯的工作。香港在二次大戰中淪陷後,《大光報》遷至粵北韶關營運,萬人傑隨大隊北上,擔任總編輯及粵北分社社長。
抗戰勝利後,萬於一九四六年重返香港,先後任職《工商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晚報》和《中文星報》,除了負責編務、撰寫社論和政評專欄,他在三十代後期已開始以「俊人」為筆名,寫了大量文藝言情小說,多是先在報章發表,後出版成書,估計超過二百三十多本。「俊人」這筆名走紅後,萬人傑於五、六十年代,曾與友人在旺角合辦俊人書店。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其中由岳楓執導,樂蒂主演的《畸人艷婦》,一九六一年在亞洲影展中獲最佳編劇獎。
何智明在戰後經朋友介紹,與萬人傑認識,一九四七年結婚,育有一子一女。她形容丈夫個性剛直仗義、不拘小節、嫉惡如仇。一九六七年初,他眼看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禍延香港,便棄寫文藝小說,開始用萬人傑這筆名,專注在《星島晚報》撰寫《牛馬集》、《左道旁門》等政論專欄,強烈批評中共禍國殃民,煽動香港極左勢力,在香港製造事端,破壞社會安寧。那些擲地有聲的文章,迅即得到廣泛支持。他與當時經常在電台節目譴責左派暴行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原名林少波),堪稱那年代的反共健筆和名咀,亦因而成為左派暴徒的眼中釘。
同年八月廿四日,林彬與堂弟林光海駕車上班途中,慘遭伏擊。兩名扮成修路工人的凶徒截停林駕駛的汽車後,放火將二人燒死。萬人傑同樣亦接獲死亡威脅,但他堅持留在香港,繼續對左派暴行口誅筆伐。
林彬逝世後兩個月,他針對毛澤東用來迷惑人心的《毛語錄》,出版《萬人傑語錄》與之大唱對台。十一月五日又創辦政論周刊《萬人雜誌》,邀請漫畫家嚴以敬(筆名阿虫)設計封面,張贛萍、何家驊(筆名岳騫)、程靖宇(筆名今聖歎)、焦毅夫、何水申、曾憲光等名家撰文。甫出版,便大受歡迎,銷路節節上升。他不時聯同一些作家與支持者茶聚,研討時政,期間有人倡議成立萬人協會,以團結更多力量。該會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侵佔中國東北的紀念日正式成立。
資深會員陳先生表示,讀萬人傑的文章,常感到一股浩然正氣,抒發出自己的心聲和鬱結。協會那時凝聚了各行業市民,人才濟濟,高峰期,會員多達千餘人。萬人傑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侵華的盧溝橋事變紀念日,再創辦《萬人日報》,得到很多會員無私支持,他們除了協助萬人傑處理出版業務,亦定期舉辦研討會,及發起聲討中共惡行的抗議活動。
一九七五年由大陸移居香港的作家劉濟昆,數年前曾在其報章專欄指出:來香港後讀過反共文章千萬篇,罵得最出色的莫過於萬人傑,他寫得比蔣介石更好,左派寫手望塵莫及,中共實有必要研讀《萬人傑語錄》。他十分贊同萬的說法:「站穩反共立場,但不唱反共八股,也不做罵街潑婦,我們是在人性方面反共,以理性態度反共。」
就在《萬人日報》面世前一年,萬人傑遇到人生一次重大打擊,他的兒子孝昌不幸因癌病去世,年僅廿四歲。何智明表示,一對子女都品學兼優,長女孝晶考取獎學金到美國攻讀物理,之後發展自己的舞蹈事業。兒子在六九年到美國修讀電機工程,抵美七個月驗出患上肺癌,但他奮發自強,一邊積極接受治療,與癌魔搏鬥,一邊努力完成本科和碩士課程,取得優異成績。在逝世前一年多,還回港協助父親籌辦《萬人日報》。
為人積極的萬人傑雖然承受喪子之痛,但他化悲痛為力量,以兒子之名,設立助學基金,為有需要的優秀學生提供資助。他並把這次家庭變故撰寫成書,名為《永恆的愛》(另有一版本名為《永不死亡的愛》)。台灣中央電影事業公司一九七七年根據此書拍成同名電影,由丁善璽導演,盧燕及賈思樂分演母子角色,獲得第廿四屆亞太影展的最佳劇情影片獎。
到了八二年中,心力交瘁的萬人傑突然中風,腦部、左手左腳均受影響,無奈退休,專心療養身體,兩年後移居美國波士頓與女兒團聚。何智明表示,丈夫雖身處海外,依然心繫香港,關注中國局勢。在家人悉心照顧和鼓勵下,萬人傑在八七年夏天重出江湖,為美洲版的《星島日報》撰寫專欄,品評時政。
一九八九年北京爆發學潮,萬人傑支持一些學生提出「要革命不要改革」的主張,認為中共黨性殘酷,如果這次民運不能令中共放棄權力,重建政治架構,必會換來鎮壓報復,後果堪虞。他還為此與幾名友好寫了份〈向北京學生致敬書〉,闡述其觀點,在波士頓僑學界支持北京學運的聯會上宣讀。豈料遭到一些左派,甚至是當時滯留美國的大陸自由派人士,包括劉賓雁等評擊,雙方一度在華文報章上展開筆戰。而往後局勢的發展就一如萬人傑所料。
同年十二月底,萬與家人回港探親,寄住朋友家中。在聖誕前夕的平安夜,他與多名好友聚舊後,或許心情興奮,無法入睡,獨坐在廳中看電視,不久便被發現暈倒梳化上,悄然告別了人間。何智明說:「他到底是屬於香港的,直到最後一口氣都要回到香港!」
何智明其後與萬人傑一些在美國的好友,於一九九三年成立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將萬的遺產每年所得利息收益作為獎金,頒給為中國民主自由奮鬥的人士,以表揚他們的貢獻,十五年來共有四十多人獲奬。由於種種原因,基金會已於二OO七年結束,但何智明深信,萬人傑生前追求民主自由、批判獨裁政權的信念,會長存人間。當下的香港,更需發揚萬人傑的不屈精神和鬥志!
VIDEO
2014年1月號香港開放雜誌
女兒孝晶懷念父親的文章
萬人傑語錄摘篇
悼念萬人傑
(
《紀念逝去的報人》 網站二O一四年一月十二日)
(另見
《開放網》 二O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活得豪氣去有遺憾的張贛萍
許之遠
(謝謝Linda Pun提供張贛萍照片)
一九六七年,已成年的香港居民,都會記得當年的左派暴動的情景;也同一個年代,香港有一本無人不知的雜誌:《萬人雜誌》;這是由作家萬人傑出面主編,實際執行編輯的是張贛萍。張當時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了,但賣文養不起家;主要入息,還要在《快報》兼採訪記者,並負責部分編務。這種日以夜繼的生活,終於在盛年(五十二歲)中猝然以心臟病的襲擊,搶救不及而去世。張的逝世,香港讀者趕來送喪,靈堂坐滿,到火葬場也近百人;以後又發起為其子女籌集教育基金。恐怕在香港作家群中,只有張贛萍一人得讀者這樣的愛戴。
張贛萍得讀者的愛戴有其主、客觀的條件;主觀的當然是他的作品,他在文壇雖然崛起不久,但在大報已有固定的寫作地盤,他的《彈雨餘生述》,以個人在戰場的親歷,身歷的描述又如此生動,題材如此驚險,在生死俄頃之間,張的生花妙筆,既能繪聲繪影,又能夾敘夾議。香港人看慣武俠小說那種虛無想像、不吃人間煙火、打不死的紙上武俠,一旦轉入有血有肉、真槍實彈的戰場搏鬥,又夾着國家、民族大義,這種敵愾同仇,當不是全不相關、作壁上觀的虛構武林故事可比。這種新作品,張贛萍一出手就抓住了讀者,一炮而紅。繼而《血淚斑斑》、《抗日名將關麟徵將軍傳》等寫實的傳記文學;然後又發展為戰地小說的《戰地春夢》、《勁草》等;又帶有個人傳奇性的《歡場兒女》、《美人恩》、《美人怨》、《一夜之間》,都教讀者對他生平的經歷,起了驚嘆的吸引。
客觀的環境,香港比鄰大陸,那時正當「文革」,有許多動亂的傳聞:「文革輸出」第一個站當然就是澳門與香港。葡國政府乾脆表示,隨時可以撤退,要輸出就不必了,來接管就好。香港政府早期也忍耐着靜觀其變。總督府也貼滿「大字報」,土製炸彈的「菠蘿」一日三驚,隨着林彬被活活燒死,左派也公開了黑名單,連原本左傾的金庸也走避鋒頭。大部分港人縮瑟着。就在那時,萬人傑以異軍突起,在他的專欄上,天天對左派言行抨擊,成為抗暴的英雄,自然在黑名單首列;並以「萬人磔」示其下場;張贛萍就這樣鼓勵萬出來辦一本雜誌,專門對暴行抨擊。
這個雜誌發行,本錢不過三兩萬元,交到張贛萍手上實際主持編務,竟然一紙風行。銷路還遠至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書報店,仍然獨佔鰲頭,銷路可謂無遠弗屆。我也從朋友處讀到了,這一本徹頭徹尾的反共雜誌,以「文革」大失僑心,也就在僑社風行起來。張贛萍也成了能廣結海外反共人士的重心人物。所以他然突然的逝世,不但香港人追悼,連海外眾多的讀者,很多都自動匯錢到《萬人雜誌》,響應為他一門孤寡籌款,並作子女的教育基金。
張贛萍主持實際的編務外,他的組織能力亦強,他能團結讀者群,定期餐聚,以後發展成「萬人協會」;讀者能與作者聯歡,這也是香港雜誌能發展讀者群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模式。由於張老編的誠摯,很得讀者的愛戴;萬人協會成為張廣結讀者的橋樑,也成了《萬人雜誌》推銷的生力軍。左派勢力愈囂張,該雜誌的銷路愈大。可以看出當時的暴烈行動,很惹港人的反感。
張贛萍的軍旅生活,在他的作品都有他的身影,甚至是他的經歷。若論作家與讀者之間最不隔膜的,以我所認識的、算得上作家的朋友,首推張贛萍。若論編者與作者最不隔膜的,而張贛萍算是個編者的話,也是他和作者最融洽的。以張的性格,胡爵坤先生最清楚:認為張那種「落落寡合的人,不容易交朋友,也很難交得上朋友。假如交上朋友的話,將是肝膽相照、聲氣相求的真朋友,而不是勢盡交絕、利盡交疏的偽朋友。」這幾句話,真可謂觀察入微,真不枉張視他為既知遇又知己。
張贛萍是純粹的港產作家;他到香港以投稿賣文始,成名以後也未離開過香港,又在伏案寫作之際感到不適,先後不到一小時就逝世。如果我們讀過他的作品,就會知道他的豪情,賭錢算得甚麼!賭命也不知多少次。真是活得豪氣、死得爽快的、絕無僅有的、如假包換的純種香港作家:沒有一篇文章、一本作品在香港以外刊行的;成名在香港,逝世在香港,沒有假借香港以外的聲華加在他的香港作家的桂冠上;所以是個「純種」的香港作家。
張贛萍本身就是個傳奇人物;他的經歷已較吸引,何況他還有一枝神奇的妙筆,驚異的描寫,教人目眩神奪。他迅速的崛起與倏然的逝世,就像隕星一樣,劃過長空,明亮而迅速的消失,一樣的教人驚嘆。
在抗日戰爭中,以淞滬之役(八‧一三)一起,他剛二十歲中學畢業即投身軍旅,以他的智勇剛毅,擔任守陣地的大隊長以致出入敵後的諜報隊隊長,都是九死一生的經歷;喝馬尿、臥棺材、沒有麻藥割肉取彈頭,重傷死而復生,張在八年抗戰中都經歷過。
張贛萍在國共內戰中,國軍在京滬失守之後,才帶着父親和弟弟來港,他到打石場做挑夫維持生活。由萬華清先生帶他離開挑夫、打石的行業;以後又由朱振聲(戎馬書生)、胡爵坤先生帶他走入作家的行列。他以後和太太谷志蘭結婚,在《彈雨餘生述》也有一段「夫子」自道的記述:他一生只寫過一次工工整整的信,「那就是追求我黃臉婆時的第一封戀愛信,等我追到了,又是『鬼畫符』了。」「我們結婚不但沒有嫁妝,窮得連一套新衣服也沒有,穿的西服,也是向朋友馬定波借的;更可笑的,連洞房花燭夜的床也沒有,我原用一塊門板做的單人床,也不過是在單人床櫈上加釘兩條橫木,另外加一塊木板,由單變雙而已。在我所有親友之中,我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對窮苦患難夫妻。」結婚後到懷着第三個孩子的時候,張太太以營養不良和操勞過度,得了肺病,那是一段最艱辛的歲月。過了這個厄運,張太太的病好了,也找到工作了。張贛萍的寫作生涯也開始有收穫,第四位幼男也出生了。
這是他們倆結婚後最快樂的時光。可惜那一年(一九六三)新春年初二全家出門去拜年,回來時,他們的木屋、家財、藏書、手稿全被燒光了。這對苦難鴛鴦,又得含着淚水去重建家園。
就在火毀住屋的那一年,香港《快報》創立,胡爵坤先生聘張贛萍到《快報》來;也從此,張的聲名鵲起,也算擺脫過去的窮困。他的事業也看到好的前景;可惜還不足十年,他竟然沒有任何預警下倒下,結束了傳奇的一生。
我為《萬人雜誌》撰稿多年,自然和張贛萍書稿往還,他還有錄音聲帶寄來,我也準備一九七二年赴約相見,怎料到尚有半年,他就不辭而別了,我們終於緣慳一面。
我們雖沒有相見,但多年的書信往還,我們已成通家之好;當年先父和岳父尚未去世,他們倒先見面多次了。一九七二年,我還是依計劃回香港,離開香港已是十年了。當然也去探訪張大嫂,長女剛可高中畢業,找到一份航空公司在啟德機場的文員工作。其弟妹猶是中、小學生。張大嫂第一次見面就拿出張贛萍手寫的一張遺囑給我看,說明他有不諱的時候就去找我。這的確是張的遺墨遺筆,他的「鬼畫符」誰都假冒不了的。張的周慮,為了這個家,真可謂無微不至。當時長女韋弦姪也不過十八歲,我還得徵詢她願不願意遠離家庭,她真有父親那一份果敢,就這樣決定。以後我帶她到加拿大來,跟着我做事、讀書;以後她和徐君結婚,一直勤奮的進修和力爭上游,已是為人妻為人母,還是電腦業的頂尖專家,常到歐美各大公司視察與指導,她坐飛機就像在香港坐渡海小輪一樣。我從未見過有如此努力上進的時下青年,張贛萍有這個女兒,亦足快慰平生。韋姪後接母親與弟弟來時,兩妹亦早巳結婚。
目前只幼妹一家留港,餘都在本市,事業俱各有成。張太太仍健康,只稍嫌重聽而已。桑榆晚景,含貽弄孫,亦稍補過去的辛勞,憾者不能與張贛萍同偕白首耳。而張贛萍那打不死的英雄氣概,縱有兒女私情,但都不會不釋懷的,只是他的理想和抱負未實現,應屬遺憾吧!
張寫了不少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仍嫌戰場情形「一筆帶過」,他的理想作品已在腦海醞釀了十多年,主要人物都有了,連標題都想好了──《同歸於盡》;主題是反戰的。除此之外,他還計劃寫一部沒有對白,全部是心理刻劃的小說,這部小說的人物和故事也想好了,標題──《三年兩語》;寫一對每日相見的男女,暗戀三年,從未打過招呼,未正面說過一句話。等到打招呼,只說兩句話的時候,故事也結束了。這些理想終未實現。
(
《許之遠文集》 )
硝煙筆戰──憶萬人傑
沈西城
近日,陶、蕭兩才子隔空爭辯,戰情激烈,我乃局外人,難置喙,瞧熱鬧!猶憶上世紀六七年有一場文壇論戰,硝煙濃烈,勝今多耳。未說過程,先介紹論戰兩位主角:徐速和萬人傑。徐速聲名赫赫,一本《星星.月亮.太陽》名聞遐邇,名利兼得。萬人傑則去世二十多年,日落星沉,知者不多。萬人傑原名陳子雋,生於一九一七年,長徐速七歲,廣東番禺人,四六年抵港,先後出任《工商》、《華僑》、《星晚》編輯,復以「俊人」筆名撰寫言情小說,一部《畸人艷婦》,聲名鵲起,成為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作家。徐、陳兩人,一崇文學,一倡流行,粵諺云「大纜都扯唔埋」,何故會遽然反目?這正是大詩人蔡炎培老哥哥惹的禍。六五年徐速辦《當代文藝》,一紙風行,成為愛好文藝者的讀物,六七年,《當代文藝》發表了一首署名林筑(即蔡炎培)的新詩,題為〈曉鏡——寄商隱〉,這首詩招來《萬人雜誌》宋逸民譏評,彼以〈「密碼派」詩文今昔觀〉為題,重點指出這首〈曉鏡〉是「密碼詩」,評曰:「這首詩雖然是用中國字寫的,每個字我們都認識,但組成句子之後卻每一句都看不懂。」徐速基於維護作者的尊嚴,起而捍衛,寫了一篇長文〈為「密碼」辨證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徐速所持的觀點着重此詩不屬「密碼」,用詞造句,極為清晰,還旁徵博引,替此詩辯解。」(引慕容羽軍語)徐速本意除了辯誣還有出於愛護後輩之心意,豈料引來萬人傑不滿,在《星晚》「綜合版」「生活圈」《微悟集》專欄排日撰文反駁。徐速直性子,哪受得挑弄,揮筆迎戰,你來我往,殺得天昏地黑,正是:八方風雨會香江,玉堂仙客聚文壇。
筆戰持續,到了最後,批的批盡,罵的罵光,再無深意,人人都以為論戰快落幕,卻是變生肘腋,蕭牆禍起,慕容羽軍記其事云──「《萬人雜誌》那邊,發現了1969年10月20日《新晚報》副刊署名深苔〈啼笑皆非的社會調查〉的文章,指出南洋大學180名學生選出20個『最喜歡的作家』,魯迅佔第一,徐速佔第六。文中更指出:『這排行第六的作者是誰?』隨即說『就是《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而《星星.月亮.太陽》,乃是『抄襲抗戰時的一本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東西,但是抄得比原來小說差多了。』」萬人傑得知,喜上眉梢,在《萬人雜誌》發表文章,直指徐速抄襲姚雪垠,同時許下重金徵求《春暖花開的時候》一書,於是「密碼詩」聲滅,討伐「抄襲」怒潮勃起。徐速面對質詢,憂心怔忡,連忙約晤慕容羽軍茶聚,因他知道慕容羽軍南下香港時,身邊僅帶三本書,《春》書是其一。慕容羽軍不欲多事,對徐速說「我有這本書,但我有堅持,我的書絕不借給別人!」徐速這才釋懷。若干年後,徐速已逝,我跟慕容兄晤面,詢及此事:徐速是否抄襲?回道「不敢說,可受影響是免不了的。」回說筆戰,如火如荼,徐速筋疲力倦,終乞徐東濱代斡旋,始寢其事。
八十年代初,徐速遷居北角麗池,望衡對宇,跟我成為鄰居,偶然我會到他家吃早餐,提起筆戰,徐速餘怒未息,憤然道:「西城!我徐速怎會抄襲,那對不起讀者,更對不起自己!」越一年,徐速病逝,享年五十七。萬人傑我僅見過一面,七一年隨報界前輩往詣「萬人協會」,聽萬人傑講演,慷慨激昂,銳利如刃,他說「香港共黨搞事者,什麼都自稱『愛國』,愛國乜,愛國物,彷彿愛國是他們專利品,別人休得分享。不過,他們的愛國是自稱而已,事實上呢,他們不但不愛國,而且是害國。」此言於今仍適用。八九年平安夜,萬人傑去世,得壽七十二。
(附記:巴黎恐襲,世人多咒罵恐怖分子而怠於追索其由,竊以為清本正源,方可得和平。)
讀者留言摘錄
芝士有識:
憶當年萬人傑為文,極其反共。
其後愛子英年早逝,寫了多篇文章悼念,千元西服陪葬,印象頗深。
又其後,與另一寫手(姓馬?)聯手,連月筆戰胡菊人,更寫《胡笳十八拍》文章十八篇,連環攻擊,極盡挖苦,用字辛辣無情。
本小子當年,已有不以為然之慨~
Fengshui Leung:
萬人傑後來在快報又與田雪筆戰。記憶中應是四人幫後期。其時田雪在快報有專欄專寫大陸政壇小道消息。
Perry Yung:
萬人傑行文用字簡潔俐落,言簡意賅,老嫗俱解,他在上海街附近經營的俊人書店乃我幼時留連打書釘之地,他的萬人什誌俟六七暴動後更是獨領風騷,洛陽紙貴,可惜晚年反共反到走火入魔,文章淪為反共八股,了無新意,又喜到處樹敵,話說當年梁小中邀請萬人傑在大中報開一個副刋專欄,誰料day one就和其他專欄作家開火,唔係一個,係全部!記憶中只有醉茶集的作者冇同佢反面而已!
Yu Lai Mei:
《星》書舊版好看,新版結局將女主角亞南斷腳改成……
傷盡讀者心。
Nicholas Parker:
那詩說的明明是魚玄機的故事,卻又要「寄」不相干的李商隱,有說是當時戀上有夫之婦的蔡炎培自比於與魚玄機作不倫戀的溫庭筠,並向友人傾訴斷腸的夫子自道來者。貫徹全詩都是性的隱諭可不須怎樣解碼,當時萬人傑就二話不說將之惡搞成鹹濕文字。右傾言辭一向辛辣的萬,損人那得留有餘地?
至於那個吹雞說徐抄襲而再掀罵戰的「深苔」,有說不就是日後以相學聞名於世,今也已歿的林真。
俱往矣。猶記萬人雜誌當時封面與插圖常用嚴以敬(今之阿蟲)漫畫,粗墨素描禿胖老毛、粗眉林彪,俱躍然紙上,於今憶來,恍如昨日。
Nicholas Parker:
豈敢?弟當時只黃口小兒,好奇翻閱家中大人買的雜誌,當讀到「咸宜觀有人疾書、那一筆寫在未濃的墨上、重新跌望背壁的觀音、是魚是鳥是最玄的女體」與惡搞者的解讀時,也不禁莞爾:係喎,又確係廚房階磚嚟。
Nicholas Parker:
那些年,沒有性教育這回事,遑論互聯網。我們都是在好奇與摸索中一路走來。
Jacqueline Tong:
我读过万人傑的作品。非常反共。
当时他被左派报纸视作眼中钉。记忆中他的儿子早逝,还得到某报庆贺。
Mancheuk Tsang:
我讀過二者的書,我相信徐有意抄襲。
Hinhing Wu:
事實上,徐速是有將《春暖花開的時候》翻印的。本人手頭上保存了一冊。
徐速一個「好戰份子」,除本文所述外,他還伙同黃思騁跟盧森和他的《文壇》罵戰;也為了仲實寫了一篇揶揄徐速文風的「紅燒清燉之類」而砲轟《新晚報》。十分之「火」。
(
蘋果日報 二O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