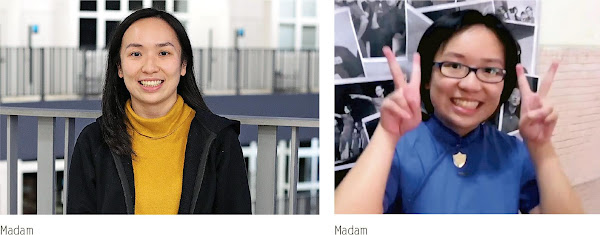【《給十九歲的我》女生自白1】紀綠片女生阿聆親撰萬字長文表達心聲 質疑受訪者權益沒受重視 呼籲校方保護學生私隱
(編按:由英華女學校委約,著名導演張婉婷歷時十年攝製,追蹤六位女生成長故事的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自去年首映後即引起熱議,上月更取得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然而,坊間也出現評論對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和呈現方式提出質疑,帶起對紀錄片倫理問題的關注。片中女生阿聆早前主動接觸本刊,表達其個人想法,對紀錄片拍攝過程和導演處理方式提出質疑,以及她曾就公映問題多番跟校方交涉不果。阿聆現親撰萬字長文,交由本刊獨家刊登,以下為原文:)
阿聆自白:
看到坊間最近不乏討論《給十九歲的我》的倫理問題,有指所有被拍攝者均支持《給》上映,因此該討論是無風作浪,繼而網上萌生了我缺席宣傳場合是因移民之說。作為《給》的主角之一,我從來沒有公開表明我對紀錄片處理手法的看法,或是否同意放映。此文目的除了表達我對《給》的想法外,我更希望的是不要讓有建設性的聲音和理性討論被抹煞。其中一篇深深觸動我的文章出自吳芷寧小姐手筆,不單是因為她筆下的情形恰巧大都應驗在我身上,而是即使全部拍攝對象都同意公映,受訪者的權益、保護學生私隱等都是重要課題。正正因為《給》是一套史無前例的學校紀錄片,更要慎重考究當中細節。
首先,我希望表明我贊同《給》在教育的價值,我在英華六年,學校給予的空間和自由度是真真實實的。
但我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亦在知情後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張導演。無奈最終校方及攝製團隊在此前提下選擇了公開放映《給》。當中牽涉太多時序及事件,但我希望我和另一位片中主角 (編按:本刊另一篇報道的阿佘 )的分享能盡量填補現存討論的漏洞:
1. 電影公映的正當性
還記得導演在校內宣傳時分享中提及要剪輯十年的海量片段的過程十分艱巨,我亦難以想像團隊在當中付出了多少血汗,並衷心欣賞並敬佩團隊的努力。不少觀眾觀看電影後都感歎在現今網上資訊流通的時代,如此赤裸地呈現自己的過往實在不容易。誠然,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而我與其他數位在final cut出現的同學在校內首映(2021年12月)半年至數月前才首次接到通知我們校方和導演有把電影公映的打算。由於不少當年在校內見證着拍攝過程的學生,校友,甚至拍攝對象如我對放映的理解一直是供校內放映/籌款用途(例:如校友捐款就可獲贈DVD,因我們一直以來都稱張導演的團隊為「DVD team」,通訊群組亦以此命名),校方截至上述時間亦從沒表達紀錄片會用作公映,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及參展電影節等用途,由拍攝計劃開始至校內首映之前,校方亦慣稱他們為「DVD team」。在此前提下實在令我難以想像張導演及學校有公映的計畫,並懂得就此安排提問。
十年之久的拍攝時間,莫說是導演,作為當事人的我也不能清楚記得十年到底被拍了些甚麼。即使我對電影的前期認知是校內放映,對於放映後我能否承受各種閒言閒語,我是擔心的。就此我曾不少次間接透過校方,及直接跟導演反映希望得知剪輯內容,故事大綱等。導演以每個人都要求刪這段刪那段的話紀錄片便剪不成的理由拒絕。甚至到校方通知我電影有公開放映的可能,以及2021年12月校內首映前,校方和團隊從來沒有給予我觀看任何片段的機會,並在沒有知會各主角的情況下把final cut片段送往電檢。我是在校內首映時,與當時的觀眾一樣,第一次看這齣電影。
始終校內和公開放映的本質上存在太大差別,知情後我亦有不斷反映我對於公開私隱的隱憂,以及我事前不知道有公開放映的打算。校方由得到我父母簽署的同意拍攝通告後,到校內首映後,從來沒有就拍攝的進度和用途和我父母再作任何溝通。校內首映後,校方代表得悉我以及另一位拍攝對象首次看到電影成品後有情緒不穩的狀況,表示沒有意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並向我說:
「千萬不要覺得我們(校方及攝製團隊)是刻意bypass你,因為沒有可能的,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直接引用校方錄音)」
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
多麼理所當然且合乎常理的說法。但為何校方在校內首映前不debrief我們並確保得到各人同意後才放映?不過始終校內首映受眾很有限,都是校友,所以接下來的討論有關consent和公映的安排才是重點。
校內首映之後,校方代表和導演嘗試了解我感到不適的原因。他們不解我為何由幾個月前配合學校宣傳,到校內首映後我的反應之大。我解釋因我不願意及認為沒有要讓電影公開放映的責任,多年來的配合都是因為我從不知道電影有公開放映的打算,甚至我在校內宣傳活動時拍的訪談片段時我亦沒有看過電影,我是從張導演口中知道電影大概會是這樣,希望我可以幫忙宣傳給校友。而在得知校方及導演有公映的打算後,我亦不少次跟校方代表及導演分享我對向公眾(而不是原定的校友)公開私隱的顧慮。我在觀看電影前沒有很強硬的反抗公開放映是因為校方代表及導演以此片能對他人有正面影響等原因循循善誘,我亦認為我應該先觀看電影才能評估我能否接受讓校外的人觀看我的片段。而首次觀看《給》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恐懼並拒絕《給》公開放映,這個想法亦有充分地反映在我的情緒上──我需要並有即時向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求助。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我的狀態,電影是不適合進行公映的。
為更深入了解事情有沒有扭轉的空間,校方在2022年1月首次提出private screening和電影節之說。校方以紀錄片訊息正面為由希望我能考慮同意讓校外的人觀看,並多次強調拍攝團隊的努力需要得到回報。我強調只要是讓校外人士觀看電影此行為本質上已有不妥,如果校方和拍攝團隊堅決要對外放映的話我不能同意,並要求導演把我的相關片段全數剪走,導演以final cut已通過電檢為由拒絕。另一方面,校方亦承認他們應該要處理得更好。如是,討論未能達成共識並一直膠著。校方代表亦有不斷私訊我關心我的狀況,我的態度依然是堅決拒絕private screening和電影節的提議。校方在這期間亦有與其他拍攝對象交涉,草擬了一份consent form,簽了就等於我們親自授權校方進行private screening和參與電影節。我至現在亦沒有簽署此文件,而其他五位主角已簽署。
但這一份consent form在半年後便被校方,導演和監製以一份我父母於2012年簽署的「通告」徹底推翻。
2022年6月,校方代表聯絡我再次進行游說,希望我念在拍攝團隊多年來的努力,至少讓他們private screening。我認為原則上我是絕對可以不作出任何讓步,但校方代表是我在校時的恩師,而她亦似乎因為事件膠著太久已開始受到不同壓力並有情緒。那一刻我不願看到她難做,所以答應她我會讓步與拍攝團隊溝通private screening的可能性。怎料導演和監製原來是打著要我同意private screening及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念頭和我進行討論。討論中最大爭論是在於電影節,因參展電影節後是需要有公映場次。導演和校方代表強調只是一兩場的場次,沒有人會看的,叫我不要介意。為何說服我的角度和原因是由觀看數字主導,我們要面對的已經不單是校內的聲音,你們不是應該有責任解釋清楚電影公映後片中的人物角色會受到怎樣的評論,以此為出發點去讓主角,甚至他們的家人去考慮清楚利弊後有自主權決定上映與否嗎?十年來至現在我撰文的一刻,我從沒在校方或攝製方聽過任何有關此方面的溝通,他們不斷以電影訊息及主角形象正面為由去作游說。我亦不明白為何要參展電影節,電影本身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紀念學校重建,而不是參加電影節角逐獎項,而且連帶公映場次,已經遠超於原定的討論範圍,因此我表示反對電影參展。此時,校方首次拿出了2012年我父母簽署同意我參與拍攝計劃的文件──
《給》中的「阿雀」在訪問中形容因簽了通告所以繼續拍攝。其實不單是阿雀,我對父母於2012年簽署的文件的理解都是通告。在最抗拒紀錄片拍攝的時段,我和其他被拍攝的同學不約而同的在校方及導演面前不時提及通告一詞。我們當時的理解是因為父母簽了通告,所以我們需要參加拍攝。至拍攝計劃將完結之時我們亦不時戲言那份通告是「賣身契」。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校方、導演和監製在參展電影節游說不果後,第一次把「通告」的正本呈現於我眼前──原來我多年來以為是一份簡單通告,竟然是有如此詳盡細則的同意書。校方、導演及監製稱他們已經尋求法律意見,如果我仍要繼續阻止的話有機會有法律責任。即使我沒有簽署任何文件,我在成年後仍有繼續參與拍攝的行為是給了silent consent,是有法律約束力的。
Silent consent?我甚麼時候給予公開放映silent consent?我不是說了我多年來的配合是基於我不知道電影會公映啊。又,不是說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嗎?
阿聆一直以為開拍前父母所簽的同意書是一份簡單的通告,直到去年校方拿給她看,她才知悉同意書的內容。(圖片經過處理,遮去名字、簽名及私隱。)
我認為校方及導演選擇在這時間點才解開此誤會的處理對我是很不公平的。既然我十年來由始至終使用的是通告一詞而非同意書,即代表我沒有意識到有一份法律文件的存在。不知其存在,又如何入手去了解當中條文。如果打從一開始校方及導演認為2012年簽署的同意書已經凌駕一切,那為甚麼在有拍攝對象表明反對再作放映時會出現第二份同意書?
我認為再與導演及校方代表周旋意義已不大,並留意到同意書上是只是授權英華女學校,因此我主動要求與校董會進行對話(2022年7月),我表示我可以有條件地同意private screening和電影節(例:如需有公開場次必先要與所有拍攝對象溝通並得其同意,刊登任何宣傳物料前須知會拍攝對象等)。我亦有準備一份詳盡文件列出我的條件及所有理據以供參考。但校方的回應電郵如下:
“The IMC treasured the chance to hear from you and your father yesterday. Upon deliberation, the IMC has decided to allow the documentary “To My 19-year-old Self” to participate in film festivals and private screening initially for one year. The IMC will then review the situation.
Please be assured that the IMC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the filming team and also the filmed subjects.”
單看電郵,校方完全沒有嘗試解釋他們的觀點,為何他們認為沒有學生的同意公開其私隱是可以接納,亦沒有表明是否會按我提出的條件行事。我主動要求了解原因後,校方才安排一次會面作解釋。而會議的內容是通知我其實電影已參展,只是一直未能得到我同意沒有過多宣傳,對於我提出的同意條件,校方也沒作回應。校方又再強調不明白我為何倒戈,一邊認為我的憤怒和我內心的想法不成正比,給我提供情緒支援,一邊不斷以同意書的法律約束力去強調學校的決定有法律依據。
又是同意書。難道「我」不能是一個理由去終止公開放映嗎?
對於他們的反應我是感到很害怕的,因為我在學時他們的確是我很尊敬的人,但現在我好像完全不認識他們。我的情緒開始由憤怒變為害怕,再變絕望,似乎我已經用盡方法多次跟不同的決策者去表達我反對公開放映的原因是在於本質,校方和導演都聽而不聞。我問:
「(放映及電影節)甚麼時候會完。」
校方聞言,回應說不曉得。導演亦回應過,如果電影節得獎,將會參加更加多電影節,她亦不知甚麼時候會停止播放。
你們一開始說要我的consent。之後說因為有同意書所以其實不用也可,但會尊重我。現在我提出條件嘗試去作妥協,你們沒有回應,並原來一早已略過我的意願參展,這能算得上是尊重嗎。我意識到我已沒有方法可以去阻止校方及導演做任何事情,因為連我的意願在他們眼中看起來都是多麼的微不足道,連想有一個結束的日子去盼待的權利也沒有。
其後我在社交網絡不斷看到紀錄片參加電影節的宣傳,甚至有海外公開場次。學校均沒有通知我相關事宜。在沒有心理準備底下看到有關宣傳的話會對我的情緒控制或多或少有影響,故當初提出要刊登宣傳物料前想事先得知,而提出這條件亦是因為我願意努力嘗試去配合。但學校在完全知情的情況底下選擇不作出通知。我亦有向校方幾番查詢究竟有沒有公開放映的打算,校方才告知有此打算並已在安排,並再以同意書作根據。校方和導演曾表示即使他們在法律上給予他們公映的權力,但也會尊重我,如果再有考慮正式公開放映的想法,校方和導演一定會尊重我的意願。我不斷質問校方及導演,到底他們想得到些甚麼呢?私人放映也放了,電影節要參展也參了。你們所宣稱的「教育意義」和認證團隊努力也都做到了,究竟要不惜犧牲我也要公開放映的目的是甚麼?校方和導演依舊以同意書作根據。並告訴我其實他們已簽署了發行商,就算想改也不能改了。他們不斷認為我是因為拒絕接受電影中的自己而discredit我一直主張的本質問題──
我從來沒有給予公開放映的consent。
2. 校方對我不滿的解讀
校方和導演在討論過程中不斷着墨於為甚麼我不願意公開對我個人形象如此正面的片段,亦收集不同校內首映的意見嘗試去證明及游說我。但我要的不是形象工程。考慮同意公開放映與否時我認為焦點不應放在被拍攝對象的形象是否正面,而是這個決定本質上(能否獲取學生同意)是否正確,並且主角是否清楚了解並接受其面向公眾是有機會受到抨擊的。
在最後一次與校方及張導演的會面中,校方及導演指出因為導演已與發行商簽署合約,即使我反對他們亦無力改變任何事情,無論我準備好與否,公映都會如期進行。學校會提供心理醫生對我的情緒作支援,亦願意在正式宣傳片,給傳媒提供的照片等等公開宣傳電影的場合把有關我名字和照片都抽走。我感謝學校願意作出這些修改,但這一切一切都沒有回應我對於整個程序不公義的申訴。本質上就是我沒有同意。越跟校方和導演溝通,他們的回應越令我覺得我沒有再掙扎及反抗的餘地。我無法詮釋校方及導演是抱著甚麼想法去接受專訪,說他們愛學生,視她們為女兒,但在面對我的質詢時卻只能搬出2012年的同意書及發行商事件去作為無視我意願的確據,以及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我會因電影自身的意義而交出我的私隱。
3. 校方應在學生和拍攝團隊之間做好橋樑之角色去處理倫理問題
十年來校方在拍攝計劃中的介入近乎零,溝通拍攝工作和處理同學不滿的情緒上亦是比較混亂,甚至沒有太多溝通的。可能其用意希望給予製作團隊有足夠空間發揮,我在拍攝過程中有任何不滿我不太會想起向校方表達,因為即使向老師反映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是提議我們繼續合作。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去停止拍攝是親自向攝影團隊反映並逃離鏡頭。然而導演在戲裡戲外將我們想反抗或想退出的想法是因為我們反叛,不明白作品對我們和學校的意義,我們日後定必會感謝導演記錄了我們的成長片段。我是很感激導演記錄了如此珍貴的片段,但似乎校方和拍攝團隊在萌生公開放映的念頭時並沒有考慮太多如何保護我們的私隱,以及嚴重高估我對公開放映的接受程度。我認為學校有此想法是有違自己作為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立場。同學途中反對拍攝計劃之時,學校及攝製團隊都沒有好好梳理學生反對拍攝的原因為何,只是草草用反叛的原因作結案陳詞。
整個嘗試獲取我同意的過程最令我無所適從的是校方的朝令夕改,由以學生意願出發,到只用法律角度去解釋所有問題:
2021年12月校內首映之後稱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並嘗試游說參與者考慮private screening和草擬新一份需要拍攝對象親手簽署的同意書
2022年6月後更改說法為2012年的同意書已經賦予攝製團隊公開放映的權利,但定必會尊重同學意願,暫時只會考慮私人放映及參展電影節
2022年10月再更改說法為不論我能否接受,由於已簽署發行商,公開上映定必進行
我不是法律專才,不敢妄自揣測此同意書的法律效力及正當性,但明顯存在著紀錄片的創作者及受訪者權力不對等的問題。張導演不是第一次執導紀錄片。於2003年放映的成龍家族紀錄片《龍的深處》正正是張導演所執導,她理應清楚一份保障創作者及受訪者兩方的consent form是甚麼模樣。同意書裡頭只有保障校方權益的條款,完全沒有提及學生作為參與者能有甚麼權利,能否退出計劃等等。對於校方和導演的說法我們是感到很困惑的,當一名學生有理有據的告訴你她為何不願公開自己私隱時,校方以法律之名拒之門外。導演要站在攝製團隊的一方,以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去捍衛自己的權益,無論我認為她以同意書作為根據的做法合理與否,我能夠理解為甚麼她執著於此,要捨棄十年心血的困難是我不能夠想像的。大膽假設校方及導演的確有絕對權利作公開放映,但校方多次更改說法的行為已反映其由2012年草擬同意書開始至2022年6月為止,對參與拍攝學生的權利為一知半解。究竟2012年校方交出此同意書供我父母簽署時,是如何確保我父母清楚知道我的權利是甚麼。
我亦理解張導演為何稱自己得到所有受訪者的consent,的確如果單看2012的「通告」,根據導演監製和校方的說法,校方將《給》公映的決定似乎在法律上是無懈可擊的。但作為一間學校,在公開學生私隱的片段時單以法律作為依歸是否處理得過於粗疏?攝製團隊的專業是電影製作,他們從製作者的角度進行游說也是可以理解的。李石玉如前校長於訪問中曾經提及學校把關的角色,我認為是說得很好的。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學校作為教育工作者,理應幫學生把關,處理好學生情緒,甚至應再進一步,去協助拍攝團隊由倫理角度去梳理事件。但學校選擇的是和拍攝團隊同一陣線的單在法律角度出發去找事件的突破點,我是感到詫異的。先不評論拍攝團隊的倫理意識,社會對於學校的道德要求是比其他個人及團體機構高的。校方可以認同創作者有法律根據,也應該協助創作者去理解及尊重學生意願。
我父母授權的對象是英華女學校,我父親亦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是本著相信校方的職業操守簽署同意我參與拍攝。但在每次的討論,我看不到校方有這樣的自覺,而且態度變得越來越強硬。到底校方除了法律還有甚麼理據去公開放映學生的私隱?如果把同意書當中的英華女學校換成張導演,故事便大不同了,因為一個導演和學校的考量有著很大差別。偏偏同意書是賦予英華女學校一切權力,學校在整件事中的角色應該是作為學生和攝製團隊之間的橋樑,去調解雙方的紛爭,去確保學生的權益,但校方除了給予我八個月空窗期外,似乎通通都沒有做到。
校方及導演說會尊重我,卻到第一次放映前都不讓我看一眼紀錄片,沒有理會我開的條件硬闖private screening及電影節,忽視我的同意進行公開放映,而最令我失望的是──每次我說有關放映本質上的問題,校方像錄音機般不斷搬出同意書的反應。而學校在不理解和梳理我不滿的情況下強行推出上映活動及參與電影節。
4. 導演有以劇情片手法處理紀錄片之嫌
我在中二時,導演受我家庭故事啟發改編了一齣微電影(編按:2013年張婉婷執導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大師微電影」的劇情短片之一
《深藍》)。我至今仍然認為張導演在處理微電影是沒有任何倫理問題,亦不覺得私隱受到侵犯。因為那一套是劇情片,而不是紀錄片。我和我的家人亦沒有對導演的剪接有任何意見,因為我們尊重導演在劇情片上是應該有絕對剪輯及創作的權利。但紀錄片並不是同一回事。而導演和學校在處理我對於公開私隱的擔心時,經常以「演員」一詞去表達他們對紀錄片的看法。但這不是劇情片,我也不是在演戲,我是學生啊。
我不打算評論我對於製作團隊在電影裏對我個人的詮釋是否正確,討論我對戲裡自己的主觀感受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公平公正的答案。我希望討論可集中於程序公義及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取態。客觀事實是拍攝團隊與每年大概4至5日的採訪鏡頭外,雖然一年會有約一回飯局,但此外我與團隊的交集不多。而且片中主角高達六位。我相信以張導演的專業,她定必會將她對拍攝對象的想法毫不修飾地呈現在紀錄片,亦正因如此,吳小姐的文章亦指出導演以旁白身份主導電影情節及詮釋有不妥之嫌。誠然,在對拍攝對象有限的認識及篇幅的限制底下,導演如何確保在每人只有十多分鐘的片長內,各拍攝對象的故事能被忠實呈現?對當時被拍攝對象的了解,又有足夠深度去賦予導演對我們的行為作出公開評論的權力嗎?團隊亦沒有試圖去跟我討論和考證他們熒幕上呈現的我是否貼合現實,如果有分歧,理據又是甚麼。
導演及校方不斷主張及認定鏡頭下的我就是真正的我,強調我不肯公開自己就是不接受自己的表現。我認為這說法是偷換我保護自己的私隱的想法為否認自己。而校方是憑甚麼確據相信一個與被拍攝學生的距離如此遙遠的攝製團隊所呈現的畫面是真實的,確保她們的言辭不會被扭曲?
5. 導演提問容易令人反感
在計劃開始拍攝的時候,從導演口中問的問題,即使只有12歲,我都意識到團隊似乎是因為我的家庭背景而選擇我進行拍攝。拍攝中我很常被問到的問題是:
「你弟弟現在怎麼樣?」
「你最近有沒有跟家人吵架?跟家人關係如何?」
對於團隊問這些問題的動機我是明白的,始終人家要了解我才知道應該如何拍攝我的故事。但似乎問了幾年都是問這樣的問題,我也開始感到採訪疲勞,而且我對團隊問問題的技巧是很有保留的。我印象中提問不時以負面的詞語形容我與家人的關係。其實這樣的提問,對於一個初中女生而言是難以招架,聽着也覺得難受的。而電影呈現反抗拍攝的事件時,亦似乎沒有清楚向觀眾交代事件是如何平息的。
6. 對於與攝製團隊有互信之看法
導演在採訪中提及有同學以粗言穢語罵拍攝隊,嚇得他們不敢再拍並明白要尊重同學。我倒是想反問,要逼使同學以此極端的方法去反映自己的不滿拍攝隊才願意停機,相信並不是一朝一夕的怨氣,拍攝隊自身是否也欠缺自省能力才會導致此局面?
導演亦提及,不想拍只要跟她說一聲便可以退出。她在電影中亦有提及拍攝計劃因受到同學極大反對而面臨中斷的危機,但多年來只有一位同學成功退出拍攝計劃,她由中一哭到中五,哭到全級都知道她根本不願拍攝,但拍攝團隊和校方花了五年的時間才「認可」她退出計劃。既然導演這麼了解我們,為何別人花了五年時間她也好像不太尊重同學不想再參與的決定,甚至在她「退出」了仍會不時拍攝她。我在拍攝期間亦想過退出,但最後沒有的原因是,在我眼中,我感覺到攝製隊對我們躲避拍攝的不滿,而大人們在一個十多歲的女孩面前展露出不滿的一面其實對於女孩來說是很具阻嚇性的。這亦是我一直以來不太敢直言對攝製組不滿的原因。其次,從校方和導演的說話當中,他們好像很真誠地認為我們被選中為主角是很幸運的一回事,小時的我其實也不太懂,所以某部份合作的心態是我認為我要put effort去試一試,看看用時間是否能感受到他們所說,拍攝團隊其實是成功說服了我繼續嘗試的。因此到現在我認同電影是有它的價值,但單憑電影意義本身並不能夠把公開放映的做法合理化。最後,亦是最重要的部分,團隊認為我們知道的,和校方向我們表達的有頗多出入。我必須再次強調校方由得到我父母簽署的同意拍攝通告後,到校內首映後,從來沒有就拍攝的進度和用途和我父母再作任何溝通。在退出拍攝計劃事件中,校方沒有把我們的家長叫來,製造一個safe space去讓我們決定,並詳細討論如果接下來繼續拍攝的話我們的commitment是甚麼,現在校方對於片段用途有甚麼打算。這些討論是十年來一次都沒有做過的。每一次的討論都是我直接跟校方或攝製團隊對峙,這做法對法律上的minor似乎不太公允?而攝製隊在此前提下莫名地堅信我一早已得知並同意公開放映是令我感到驚訝的。
到我稱一直不知道公開放映的打算時,張導演翻查了很多影片片段,找到了一條證據說明我中五的時候已清楚知道電影會公映。我便奇怪了,我們之間好像沒有信任?其實只要問一問其他幾位主角都能夠核實我所說的是否真實,還是導演不相信我們呢?她是有多不相信我說的話才會翻查一堆又一堆的片段去試圖推翻我的說辭?片段中的內容大概是導演說找到了發行商播放電影,另一位同學大哭,我安慰她說觀眾都是看一次便會忘記,希望她能看開點。我當時對於發行商一詞的認知是總之他們的電影似乎成形,能播放了,發行商可能是幫他們發行DVD及安排播放的人?我的理解仍然只是用作校內播放。而導演當時亦沒有就發行商一詞作出解釋並與我核對大家的理解是否一致。
作結
2022年6月至今,我多番掙扎應否公開此事去作煞停。我想我之所以到現在才公開,是因為我的忍耐已到了臨界點。校方及導演的行為不斷地挑戰我的底線,我有迫於無奈,也有被強迫的讓步,但校方和導演在此事件上到底作出了甚麼讓步?校方甚至告訴我如果我公開討論事件,現在電影正評那麼多,我公開此事的話受到的傷害可能更大。我一直記著此話,優先場放映開始後清一色的正評是讓我感到無比恐懼的,因為這似乎證明著校方所說的話是對的,至上星期才開始陸續有質疑電影有倫理問題的討論出現,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我記起校方當初試圖說服我公開放映時,我曾跟她們問這本來不就是DVD project嗎,校方的回答是DVD不是一個選擇,因為它會永久讓持有者保有我們(主角們)的片段,這對我們的傷害是永久的。看到電影叫座甚好,下一步自然是發行DVD,甚至放上網上串流平台等。經過這一切,我對校方已經完全失去信任。我就此詢問校方,校方的回覆是要再作討論。還能有甚麼討論呢?你們當初開宗明義說這樣對我傷害最深,不是一個選擇,上一次我相信你們會討論,殊不知閉門討論後的結果就是沒有得到我同意就做公開放映了。校內首映到現在整整一年時間,我其實只是不斷問校方和導演一個問題:是學生重要還是作品重要。他們從沒正面回答過。我本以為他們心裡其實清楚他們做的選擇之沉重,會盡量低調處理紀錄片事宜。但看到鋪天蓋地式的個人專訪,有關他們教育理念的報道,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甚至網上不少人給一眾主角代言,說校方已經得到所有主角同意,家長亦支持公開放映。面對著這種種,我認為我有必要將我的故事公開,因為紀錄片所面對的群眾已經不是校友的小圈子,而是公眾。
感謝把文章讀畢的讀者,給予我機會去發表自己的想法的傳媒,以及在這段難熬的期間給予我莫大支持鼓勵的家人和朋友。容許我在此引用阿雀在《大城誌》訪問中的一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還望各位尊重本人意見並給予我和家人空間。特別感謝和佩服佘的直腸直肚及率直,我還在猶豫是否要公開時佘對我說了一句話:「別人在背後說三道四不用太理會,有種面對面講。」很當頭棒喝,給予我很大勇氣。
我很喜愛張導及羅導所執導的劇情片,亦很感激學校於我在學時對我的照顧及體諒,奈何大家對紀錄片該如何處理的想法有極大分歧。不過我認為電影自身的價值及電影的倫理問題是可以分開作討論。我的立場很難去評論《給》是否一套好電影,但我絕對尊重認為此電影具其價值的看法。很可惜的是此電影處理學生私隱及道德倫理等問題實在過於粗疏,與其在電影中所呈現的影像可說是相映成趣。
最後我希望引用我在《給》片末所說的一句話:「做人要像圓規一樣,心要定,腳要走。」祝願英華女學校能繼續秉持辦學宗旨,成為師生都能引以為豪的學校。
聆
(編按:本刊已就此事分別向校方及導演團隊要求回應,詳見後續報道。)
文:聆
攝:黃家邦
(
《明周文化》2023年2月4日)
【《給十九歲的我》女生自白2】紀錄片女生阿佘曾抗拒公映 最終妥協:純粹是改變不到別人就唯有改變自己,抱這樣的一個態度
由英華女學校委約,著名導演張婉婷歷時十年攝製,追蹤六位女生成長故事的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自去年首映後即引起熱議,上月更取得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然而,坊間也出現評論對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和呈現方式提出質疑,帶起對紀錄片倫理問題的關注。片中女生阿聆早前主動接觸本刊,表達其個人想法,對紀錄片拍攝過程和導演處理方式提出質疑,以及她曾就公映問題多番跟校方交涉不果。經阿聆牽線,片中另一女生阿佘接受本刊電話訪問,阿佘同樣表達,對於拍攝過程感到不適,最初也未能接受電影final cut,亦反對公映,最終選擇妥協,接受一切,並且也願意配合電影宣傳活動,出席分享會等。以下為訪問對答:
問:《明周》
答:阿佘
問:聽阿聆說你也有些想法想分享,關於拍片和張婉婷導演,阿聆之所以找你,因為她看到有篇報道,你看到網上討論後,也有些感受,可以具體講述下,你怎樣感到不舒服?
是的。雖然我自己覺得套片,這是一個我個人需要克服、接受自己以前是怎樣的,所以我便沒有特別抗拒套片。因為我不熟悉合約或簽了甚麼consent,我也不想追究那些,我覺得套片要上映,就由得它上映。但是也有些不滿意的地方,就是我們冇份睇final cut 的version,我們是在學校內部首映(2021年12月1日)當日,我們才第一次睇到套戲是怎樣的,但那個version已經過了電檢,所以已經無得作刪改。要消化的message好多,片裏拍了很多我過去、前度男朋友,我覺得這些雖然是我的生活,始終不是你透過把口訪問我的經歷,而是將別人也拍進去,我覺得不是太好。
有一幕是英華新校舍開幕儀式之類,有邀請我們出席,我有出席,但是我提早離開之後,在學校附近吸煙,我萬萬沒想過被拍下來了。因為其實所有訪問拍攝前,都有面對面跟我們說明,會進行訪問拍攝,而那時已經沒有跟拍我們的個人生活,我覺得我活動上出現時,你捉住我訪問拍攝或影到我都好正常,但是我離開了活動,我不suppose去expect我仍然要好小心,好像有狗仔隊跟着我的感覺。我覺得她直接剪這個片段進去,而且沒有經我同意便拍攝,我覺得有點不受尊重。
在影片中,大家都知道我吸煙,也有其他吸煙的鏡頭,我覺得你想拍我吸煙,有好多機會拍,不需要這樣偷偷地在對面街zoom-in來影我,我覺得有點不太好。
問:如果當時有問你可否拍你吸煙,你會同意拍攝嗎?
其實我會。因為我都有其他鏡頭被拍到我吸煙,我覺得正面的拍攝和訪問我是ok的,但是我是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偷拍了。就好像(這個假設情形)我落街去7仔買嘢,我不會預計到你竟然會在我家附近捕我、影低我那樣。我覺得有點不太好。
問:除此以外,在紀錄片final cut中有其他令你感到不舒服之處嗎?
我覺得她說我們中三、四不想拍攝,是反叛,我不認同她這個說法,但我也不想作好多無謂的爭辯,所以我就無出聲。但我覺得以一個成年人來講,日日被人拍,你都一定會不舒服,你都一定會避開鏡頭,所以並不是因為我們青少年反叛期,我覺有少少是怪責了我們,用一個藉口,夾硬說我們因為反叛才不想拍攝。好像仍然覺得我們那時還是細路女不懂事,所以便不想給你拍攝,我覺得不能相提並論。
問:你的意思是,旁白直接將你們中三階段形容為反叛期,與你們不願拍攝,歸納為因果關係?
是的,她後來在映後談、訪問中,她同樣是說我們因為反叛所以不給她拍攝,我都笑笑口就算,我又不一定要去話她什麼不對、講得什麼不好,如果真的要問我自己意見,我覺得完全不關事囉。
問:而你那時不願拍攝,是因為干擾到你的生活、或拍攝時間太長,對你的生活有影響?
是的。因為她好似都很想搵料來爆,deep down一些的料,我當是狗仔隊或者傳媒那樣,你不想俾嘢她,她又不心息,一定要捕捉到你的故事。她可能是藝術家性格,我不識講,她好想鑽研到好深入。但我拍套紀錄片for學校,又不是for自己memorise的話,我不需要拍得咁deep,每一面都給她拍。
當然,中間有好多活動我沒有出現。他們曾經organise過去唱k,想拍下年輕人同朋友一齊hang out會做些什麼,那些我全部都沒有出現。我覺得,一來你提出這樣拍是一定不會自然,大家唱k唱得;二來就是,我覺得唱k這些活動,不是一個抽象的活動,我想大家都有去過k房,大家都應該知道唱k是什麼,未必真的好需要拍落去、未必要描述。
再者,我會覺得套戲有些旁白,我會覺得她多嘴了。有些事明明好像阿聆的case那樣,拍她和朋友之間的關係,可能拍到她的幼稚、不成熟,但有個旁白在旁邊講,說她「收兵」或者「刁蠻任性」,好似令到件事更加難堪。所以我覺得旁白上有些不舒服,有些位係不需要你特登去講發生什麼事。
問:不論是旁白說你反叛,還是旁白形容其他女仔的內容,你作為觀眾觀看時,有甚麼感覺,覺對旁白主觀?
是的,有些是加多了她的主觀想法。
問:在你的片段部分,還有沒有其他旁白是你覺得不恰當或者不正確?
其實我只看了套戲兩次,我不是太清楚記得套戲每一個細節,我大概記得有什麼情節;但是,我覺得旁白不恰當的情況並不是只屬於我(的部分),我覺得對於每一個主角,她都有講多了的位。我沒有對白(旁白內容)在手,我記不到她每一句怎樣說。
其中有一句,她說到有人問她「如何跟年輕人合作拍戲,當她們不想拍時,怎樣才可以令她們肯繼續拍?」,她說「自己要放低長輩身分,變得渺小一點,或者做我們的樹窿」。我自己覺得「樹窿」此用字,未免有點勉強。我們會同她講自己的嘢,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project是on promise的,所以一定不是真的純粹當你是朋友,自願性地將一些事講給你聽,好似是大家覺得要交功課那樣。所以如果她覺得自己as一個樹窿得到我們的信任,所以才拍到後來的故事,我覺得這樣的形容好似不是好對。
問:你意思是導演好像有點一廂情願,覺得自己成功做到「樹窿」?
我是覺得她有點一廂情願。雖然我都有跟她說,她成日話我好有義氣,明明我一開頭是最不想公開上映那位,現在讓套戲上映,還肯參加(宣傳)活動,我都是照直講,我話,不公開都公開了,咁都食咗佢囉。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問:聽你和阿聆說,觀影當刻都有些反應,其他同學是否都是這樣?
我想其他同學相對沒那麼大反應,除了Madam,因為她始終做這件事比較敏感(編按:在片中表示想做警察),其他其實都好正常,例如馬燕茹,她也很正面,都沒什麼在言行上可以給人挑剔的位,而我自己就在套戲裏有說給人杯葛,或者我俾人將一些相片放過上網,所以我對於一啲網上面或者現實生活中的評語,我自己應付到,不覺得好大壓力,但我覺得阿聆相對自尊心強些,所以這件事對她來說不是這樣的。
問:那麼你後來知道要在戲院公映,由高先發行,你有沒有反對,或者表達過意見?
我有反對的,但怎麼說,我覺得一開始他們說只是for private screening,或者在校內的內部放映,我都覺得算啦,還可接受的,但後來他們說要公映,其實我一路都不想的,加上如果套戲一定要上映,不知當初簽那份東西有沒有法律效力,如果要打官司我一定是不懂這些的,會覺得冇得討論和不想浪費太多時間,那算吧,由它去,所以我就不再繼續煩佢,變為focus多些在處理自己情緒同心態上面,都好順利,好快我就接受了,所以我就沒什麼大影響的。
問:阿聆曾說過,她第一次看的時候一看完就爆喊,情緒一直比較崩潰,你當時會不會有類似的即時Feedback給予校方,讓他們知道你的困擾?
其實都有的,譬如說套戲大多數反映出我的片段,都是一些我過去的傷口,例如話我和屋企人關係不好,我成日自己一個在屋企,我同學校關係不好,和同學關係不好,又好不開心啦,那位我前度男朋友,其實到最後我們分了手,雖然而家move on了,但bring up一些青春的戀愛回憶,難免有點傷感。即係好似加加埋埋所有事情一次過在一套戲裏,將我過去所有的傷感都揭開了,所以我當刻的情緒是很不穩定的,我都會覺得,點解你想拍一套戲,一開頭會覺得,好似將你的快樂建築在我的痛苦上面,為了拍到好的戲出來這樣,但是最後,我覺得,其實可能我睇化了,其實這些講到大眾都要睇(的電影),都係睇你自己怎睇你自己,所以最後消化完之後就好些。
問:你說當時有情緒困擾,校方有沒有安排一些輔導或者同你傾談?還是靠你自己處理?
我有跟小鳳(副)校長談過,她跟我們比較close一點,也是個比較善於聆聽和溝通的校長,她說若需要支援的話可以隨時跟她講,但我就沒有這想法,因為我也習慣處理自己的情緒,而且我本身有抑鬱症底,也很多年,至今也仍keep住食藥,我認為整部戲只是其中一個引起我情緒起伏的東西,我自己抑鬱的原因是很根基的東西,不關這套戲事,既然我能夠come over到,(片中)帶出的事,例如我跟家庭的問題、人際之間的關係,或者我在感情路上遇到的不順利,這些事導致我抑鬱的東西,可能我未完全康復,或者我又有些新的創傷,這部戲會引起我想起當時的回憶,但又未會因為這部戲而令我加深我的depression。電影公映後,我也有讀到大家的comment,大部分都是給予我支持,我也覺得,somehow是有被鼓勵到的。
問:你剛才提到,在拍攝期間,感覺不受尊重,但你也沒有強烈的反抗,而選擇默默的接受,是否有點「硬食」的感覺?
也可以這樣說,你問我嬲不嬲導演,一定會有生氣的部分。
問:她知道你嬲她?
或者她會覺得我很孩子氣,在發脾氣吧。
問:即是將你的反抗歸類成反叛、細路女、唔識諗?
對的。
曾向導演表示憂慮阿聆情況
問:你提到你有抑鬱症背景,這部戲對你有甚麼影響?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這部戲有沒有直接影響到,其實拍攝隊也好,包括婉婷,沒人知道我有抑鬱症。
問:在採訪過程中,她曾說過你有一段時間有(抑鬱症),但她應該不知道你現在還有,對嗎?
應該是,我也不想這樣高調,好像恃着自己有抑鬱症便拿多一點attention,或者被人遷就。我也不想得到太多敷衍的關心,這件事我也是比較低調的,但我也不忌諱去承認我有這種病,純粹我沒有特別提起這件事。所以婉婷就會覺得,當初學校內部討論,想徵求我們的同意(公映),就開了一個會,主角、導演、校長也在場,阿聆沒有去,那時候我也表態反對,也有替阿聆發聲,轉達她的想法,她這麼多年來,做到學生會主席又考到一間好的大學,你叫她突然之間要讓人知道她細個有這樣的action(編按:指紀錄片裏關於阿聆的片段),任何人都想躲起來,不會那麼快接受到。婉婷覺得沒什麼大不了,我說阿聆首映後都因此而不開心,正正常常的人若因不開心而發展成depression,那怎麼辦?她說:「不會吧?好小事啫,使唔使呀?」她的心態是不會預想到這件事的影響可以足以摧毁一個人的心靈。每人接受事物的能力都需要緩衝的時間,你那麼急速地想把電影公映,一急就會令impact很大,但算吧,她(張婉婷)不會聽我說,所以就有這樣的結果。
問:你認為導演聽完你的話不太在意?
我個人覺得有少少勒索,他們會說一蚊都無收,幫我們拍了好久,又會說他們也要自己出錢、pay給crew (工作團隊),一個那麼大、嘔心瀝血的製作,好似(如果)我們不讓它出街,就會浪費了一番心思。我都好明白,即是十年,不是個個都堅持到的。在我自己的平衡下,我最後覺得,我犧牲一些東西,或者我去adjust我自己的心態,都不要緊。這個位我是可以compliance(順從)到,但是不是個個都得囉。
形容為被「賣豬仔」 最終接受正面意義
問:那你會不會覺得是犧牲了自己,而去成就了她的作品呢?
我想
……其實我現在睇返那些comment(編按:指網上討論的回應),見到人們多數都是討論主角上的故事,始終這個是documentary,不是一個虛構、或者有演戲成分的一套戲,所以那些人又不會好focus地說「她拍戲拍得好好」,所以我心裏又不是特別覺得,好似成就了她一個好大、personal的一個title;我純粹覺得現在這套戲出來了,亦都有好多不同的機構,特別是教育界、社福界都看了,又或者一般人,我覺得他們有表達comment出,給我看到都是好好的feedback。我覺得如果這件事可以對那麼多人,足以造成那麼大範圍的好的impact,那我覺得不緊要啦,我都覺得我這個舉動、movement,「賣豬仔」般賣了自己出去啦,都不是一件太差的事。我覺得會給予meaning自己。
問:即是你有覺得自己是被「賣豬仔」,但是你就可以接受?但阿聆她接受不到,你會不會開導她呢?
其實我都有的,但是我覺得,即是我同她某些性格上面都似的,例如自尊心強、有些硬頸之類,但是始終不同人有不同成長速度,我覺得有時候我跟她講完,她都是那般執著的話,我又不會再去刻意多講。現在這個時間點的她,想不通就是想不通。她有不開心就會跟我講,我會跟她講如果有些什麼是影響到日常生活,你可以看醫生,不要一個人屈住,我都唯有做這些表面的支持工夫。始終都是要靠她自己去克服。
問:你們多不多在這件事上分享?好像只有你和她是可以分享,因為如你所講,其餘幾個女仔沒那麼大反應?
我和她都有傾的,因為其餘幾個的性格比較隨和些,所以她們接受訪問、說話都企理些、得體些。我說話就可能直接些。阿聆會同我講,可能她覺得我會明白她;明白她之餘,我真的會做出行動來支持她。可能其他同學都知道她不想套戲上映、知道她有創傷,但可能只是表面安慰下她,未必真的會為了她而發聲。我自己好清楚自己的立場,我知道套戲上映了,我不會因為我在套戲入面是主角而盲撐套戲,亦都不會因為當初我好不情願套戲上映,而現在要做其他事去攻擊套戲,我只是有那句講那句,有它(套戲)好的位,亦都有它不太好的位。所以我都不介意接受訪問。
問:阿聆告訴我們,她覺得在拍攝的過程中無受尊重之外,就是程序公義的問題。如果只是校內放映是勉強可以接受,但現在全世界都看到,她就接受不到,而她覺得校方是可以保護她,但最後覺得沒有。對她以前信任的機構、大人、師長,都有少少失去信任。這方面你怎樣看,有沒有同樣的經歷或感受?
我是絕對有這樣的經歷和感受,雖然我矇查查,沒她那麼機智,不會去仔細研究當初那張同意書是怎樣。我自己覺得簽同意書給你拍還給你拍,但去到公映,始終都是要整多張同意書。始終大家細個簽的,即使是父母幫你簽都好,大個了,你已是成人。因為拍攝橫跨一個未成年到成年的時間,我覺得成年的我們,應該再簽多一份。加上,因為我自己覺得,本身套戲就想拍英華重建、搬遷,suppose拍到中一去到中六,其實她就拍多了,她suppose拍六年的,點解拍超過六年,那其實這樣呢,即是當初同意書是無提及,除了Form 1簽個張,中間我們都無簽過多餘的文件
……不過算啦,由她啦,我份人就費事那麼多,好似要現在捉字蝨跟她逐樣計。
我們成日都叫她(張婉婷)老頑童,因為她個性格都是精靈嘅,都是多點子、多idea的人;譬如她偷拍我食煙,我想她都是「有殺錯無放過」,多些料整好套戲。那她拍吓拍吓覺得「幾得意喎呢幾個女仔」,就一路拍落去。她自己都無為意當初同意書的內容是什麼。我不知道呀,我覺得好難追究,始終當初大家有太多嘅misunderstanding或者miscommunication,所以我就無特別做什麼去反抗。
曾反對公映 最終妥協
問:中一簽的那份同意書,是給你父母簽署,你知不知道當中的內容?
其實是我親自簽的。
問:即是你父母亦不知道當中的情況?
不知道的。
問:你簽的時候其實也看不明白,也沒有多想?
是的,沒想得那麼長遠,當時只得十一、十二歲,不知道嘛。
問:那麼後來一段日子,就再沒有人提過件事,直至現在才想起?還是校方有跟你提過?
我已沒看過同意書「本尊」的,純粹是學校提起,還有阿聆比較清楚這回事,所以她有提過。
問:所以,即是你自從中一簽過那份同意書之後,就再沒有看過當中內容了?
是的。
問:因阿聆有提過正式公映時,其他女生也有簽過一份類似新的同意書,你清楚這件事嗎?
剛才我曾提過,有一次內部放映完之後,曾經開了個會,那一次,全世界除了阿聆都有去,但是出席的所有人只得我是未簽,因為我還想爭取一下、反抗一下。即是怎麼說呢,其實阿聆即使沒有簽那份文件,這部戲終於還是上映了,如我當初估計一樣,所以最後我做過一大輪掙扎之後,跟那些大人雞同鴨講完,我便認為算了,我簽吧,純粹是改變不到別人就唯有改變自己,抱這樣的一個態度。
問:那麼新的那份同意書是同意了什麼?
都是類似的東西,他們有權去公開放映、作什麼宣傳用途那些,所有版權歸於英華女學校等等。
問:即是你也覺得既然已經反對無效,便決定放棄,妥協簽了?
是的,因為就算我有沒有簽,反正都在上映,suppose他們需要集齊所有在電影裏出現過的女主角的簽名,才可以公映,這是當初是這樣說的,但現在阿聆死都不簽還是公映了,我也不知道同意書有什麼意義了。
問:你說的那幾位女主角就是指跟你同齡那五位?
是的,就是那幾位。
問:見到大部分公開活動,你都有出席,是因為校方邀請、既然拍了就去嗎?其實你是以什麼心態去出席這些公開活動?
其實我都是,即是我覺得自己轉換了心態,現在覺得這套戲帶給我的意義,就是
……可能我個故事比較令人深刻,好多comment都是關於我,我都覺得大部分comment都是正面。我覺得,可能我的性格同故事都令人反思、想到多些東西,都有它的意義。我又覺得,即是如果你不給一個意義自己去做這件事,你只會覺得這件事侵犯、不respect你、將你的醜事傳千里,只會令自己不開心。那我現在給個意義它,做這件事就不是一些不好的事。所以我覺得既然套戲都出街,那你就要將套戲的意義發揮出去。
問:之後如果有些宣傳、分享嘅活動,你出席都是覺得ok的?都希望帶出這套電影的意義?
是。
問:不會感到宣傳活動有壓力嗎?令你難堪、唔舒服?
不會。
問:有一點想同你確認返,因為她們拍攝是用分組導演,想問你的部分,是否都是張婉婷主力跟拍你的故事?
是啊。
因為其他分組導演我都熟,她們對我都有興趣,但是那時我好厭世,不想同那麼多人說話,Mabel(張婉婷)是最大那個,她沒其他人那麼認真嚴肅,即是可以講得笑,真的可以詰到她,所以和她說話,某程度上我覺得是舒服過跟其他分組導演說話。
問:有人說她好像以一個長輩的身份和口吻說話,但她似乎跟你說話是會平等一點?
其實她是想做到平等,她心態上,都是比較年輕,可以講話,小聰明啦,但是,即譬如話,她覺得我們反叛不拍,或者覺得她們做那麼多事拍完之後我們都不感激她呢,這一點是好固有的長輩想法。
她平時即使不想做到長輩咁,但因為她始終大過我們,受過教育嘅年代都同我們不同,所以去到某一些情況裏面,她潛意識就已經將長輩那套拋了出來。
問:你們兩個(你和張婉婷)都算相熟,換言之,你都有好多機會去溝通表達返,講給她聽個情況。
是,但是,她未必get到件事囉。
問:你同阿聆都出來講出真實想法,但是如你說,去到這個階段都正式公映,好似什麼都做不到,有些徒勞,那你覺得這樣講出來會有些什麼效果?你們可有想過?
因為聆是有expectation,她是覺得她接受訪問是想討回公道,但是我接受訪問,我真的好根據我自己個人的諗法,和一些事實去講我的意見,所以我是沒什麼expectation,我的目標只是講出來這樣簡單。
我不需要攻擊學校,攻擊導演,我純粹係,即是講真啦,我有什麼嬲她,難道她不知道嗎,她知道呀,但是她都是會笑笑口跟我講,「唔好嬲啦,你都有義氣」,即是她都會照做,那我都覺得,唉,好啦好啦,唉算啦,哈哈。
問:現在你想透過媒體或者一些公開的平台,去將你自己的真實想法給公眾知道?
因為這套戲她想呈現的是一個真實的我們,而我亦都在套戲入面,我主力想告訴觀眾,我是一個好忠於自己、好true的我,我不會因為這套戲可能有好多好評,就對於這套戲不對的事、不好的位我隻字不提,即係套戲本身就真,我個人又真,那我說話就更加要真囉,哈哈,係呀。
問:有一點補充,你講開Mabel,紀綠片中你和一個青春期的戀愛對象(拍廣告),真是廣告片,現在講出來原來是她拍的一個廣告,因為她在片中的旁白完全沒講到個導演是她的,觀眾覺得是你自己接的廣告job。
那個廣告是拍XX(編按:隱去品牌名字)的廣告,是她做導演的,因為好久好久之前,我同阿雀同阿聆我們三個幫她拍了微電影《深藍》,我們三個可能跟導演比較熟,因為我們除了學校拍攝以外,還有其他的project,所以她接觸我多些,以及可能像觀眾所說,她都偏心我多些,所以可能她覺得我會對這些事有興趣,就問我想不想過來拍廣告呀,玩下,又有錢收,當一日part-time,那我就話好了。
問:但是你拍廣告時,你知不知道她會將你拍廣告的事,放到紀錄片裏呢?
哦,那就梗係沒有啦,哈哈。
問:她還叫你男朋友來嘛?有沒跟你講,當時在拍的廣告都會是紀錄片播放片段,還是混淆了?
是,是有混淆了的,出到來,去到中間我和我男朋友受訪那個位是一個breaktime(休息時間):那時都有Cameraman影住我呢,我就知啦,那這個片段啦,應該就是學校套紀錄片想要嘅嘢,但那時才知道就太遲啦,沒理由叫我男朋友躲起來的。
問:那你會不會覺得給她擺佈了?
即是又賣豬仔。少少啦,少少啦。我熟悉她個人的性格,她做得這件事和在學校出面偷拍我食煙這件事,我完全個腦海有(想像到)她把聲,她同Cameraman講把聲,「佢喺出邊食煙,快啲快啲快啲(扮張婉婷的口吻)」,我完全是有個畫面。太熟悉她了,所以有些位是明嬲你啦,所以都費事跟她吵,唉。
問:那種熟悉,是指你不會因為這件事而震驚,又或者你認為自己根本就知道她是什麼取態策略的人嗎?
是呀,我根本就知道她是這樣的人。有陣時我都不知道我應不應該,有時我都會question自己的嬲,我想,可能我不知什麼是成功的定義,這套戲口碑那麼好,又或者她之前拍的戲口碑都好好啦,那可能對於導演、藝術家啦,可能他們都要有自己的手段,去攞一些idea或畫面,先令到套戲再上一個等級,我都會有在她的角度想下,那我想完就算啦,是的,但是我有想過的。
《給十九歲的我》導演張婉婷(右三)、發起計劃的時任校長李石玉如(中),以及受訪女生馬燕茹(左一)、阿佘(左二)、Madam(左三)、阿雀 (右二)、Shirley(右一)。
從創傷中學習成長
問:那對於你來說,你覺得人更重要,還是作品更重要?
那當然是人更重要啦,所以我當初都好想為聆爭取,我覺得,我只是作一個最壞打算,就是她可能會因為這件事,而真的有Depression,真的好大影響到她日常生活工作,或者她會有些social phobia (社交恐懼),因為始終這套戲這般出名的時候,會越來越多人知道是她,都擔心她這些情況,始終我自己是有mental illness的過來人,我都明白,那種好焦慮好無助的感受。所以我都有同Mabel講,聆有機會develop這些困擾。
這些沒得說,好似你賠多少錢給人就可以的,你始終都令到別人心靈受創,但我講就講了,學校或者導演最終的決定,都不到我左右。以及,你明知學校或者導演係一意孤行,或者一定要這樣以這種形式上映的時候,我都會希望聆可以……我有時說她硬頸呢,她真的硬頸。我們都好欣賞她這種一定要fight 到底的精神。但有陣時我都會覺得怎說呢,睇開少少會令到自己舒服一點。
問:去到這個位,你還愛不愛英華?
我
……愛㗎。
問:你仲愛佢啊?
我愛㗎,哈哈。那我愛英華不是只是,怎說呢,我覺得,我是好睇individual給我的感受,譬如說石校長對我的關愛,關校長對我的關愛,小鳳老師對我的關愛,以及有些老師對我的關愛,或者我在英華裏遇到一些好好的朋友的緣份,這些都是屬於英華的,所以沒有英華就不會有今日。還有,我對於我自己的question都是,有時我都會覺得點解自己有這病(抑鬱症),好不開心,但有時我都會覺得,有這個病才會有今日的我,才會有一個成長速度這麼快的我,所以某個程度都是所有事都要感恩。
問:其實你真是好豁達,好堅強。
我有我好難受的位的,但是我覺得如果要給一個人生的意義的話,就是一些人生觀,以及spiritual上的成長,即是你個人的physical已經成長了,我當你可能EQ那些需要磨練,你已經讀書、有學位,其實你都好多事已經完全發展了所有技能,剩下來要進步的就是,你個人怎樣看這個世界和怎樣看一些高一個層次的成長,唯有這樣。
問:你們那時11歲就寫封信,給19歲的自己,那你現在重看,你會怎樣和那陣時的自己講?
其實我可能不會講好多道理,我會同自己講話,你可能,即是當我自己對住自己的時候,可能會好悲觀,唉,你好慘呀,你自己一個,你好Lonely,那可能我會返去同她講話,你現在覺得好慘,你以後那10年都仍會經歷好多好慘好不開心的事,低處未見低,但我知道你做得到,因為可能我由細到大都相信自己是一個特別的人,怎講呢,叫不叫做一種自滿呢,我不懂講,或者是一個自信,但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是特別的,你去到那個位就會有個力量可以繼續下去。所以我會同自己講,我未來的自己會在那裏陪自己。
問:你封信應該是寫了一句:經過風吹雨打的童年才會成長……
所以就批中了,我現在真的經歷了好多風吹雨打,我亦都好滿意我現在這個階段有這樣的成長,即是如果我覺得,我不會想犧牲我過去所有的傷痛換取一個好快樂的童年。
(本刊已就此事分別向校方及導演要求回應,詳見後續報道。)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文:丘瑞欣、Chan Ning
攝:黃家邦
(
《明周文化》2023年2月4日)
【《給十九歲的我》校方回應】紀錄片惹爭議 英華女學校校長回應:我們要平衡好多方面好多人,法理情,好小心謹慎地衡量是否應該繼續
英華女校前校長李石玉如和現任校長關翰章接受本刊訪問,回應《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中有學生表示程序不公義和不尊重被拍攝者權益問題。關校長首先說,我們衷心希望,不會有任何人受到傷害。對於有被拍攝者表示不滿,關校長表示:「我們感覺上有點愕然,有點奇怪,因為我們和一眾女生,之前有一些慶功活動,一起吃飯,塵祝紀錄片的誕生,那十年完全沒有同學、家長(有投訴) 。」他承認,之前有一位同學,張婉婷導演跟了十年,但最後因覺得不願意,最後電影最後也沒有將她的片段放進去,而到了後期,他也認識到,有些同學對電影公映有保留。
「我們最初完全不是想着做一個賺大錢的project,只是一個校內紀錄同學生命轉化的過程,但當(2021年)12月1日,我們做完校內放映(編按: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校內籌款及放映活動),我們看到正面的迴響。無論是社會意義、教育意義,都是非常值得,但當我們去平衡各方面,我們有六位主角,有時我們聽到,可能一、兩位同學對拍攝手法、導演(不滿),其實整個團隊不止導演,有受薪的專業人士、家長義工、校友義工,其實我們要平衡好多方面、好多人,所謂法理情,我們基督教學校還有靈性的角度,好小心謹慎地衡量,我們是否應該繼續去做。」
他指出,同學由第一次正式看過全片到公演,有差不多十四個月的時間。
關校長:事情要平衡 也要向前看
「我覺得這是多元社會,能有不同觀念討論是好的。」石校長說。
石校長補充說,拍片意念由她提出,從2011年底到2015年,她仍在任,直至2015年八月退休。「在我退休前那幾年,完全沒有收到投訴,關於如何拍攝或不高興。」不過她同時說:「關於拍攝手法或不尊重(的投訴),我也是這兩天才聽到,當然就算是這兩天才聽到,不等於這些事不存在。我覺得大家都要公道,只是我們真的不知道,沒有人告訴我們。」她表示,就算已退休,她也會馬上着手處理。
關校長回應有同學不想紀錄片公映時說,事件上有很多持份者,「婉婷、同學都是我們的校友,手背是肉、手心又是肉。」他表示,問過校董會看法,徵詢過法律意見,亦聯絡過專業輔導人士。關校長亦提到,事情要平衡,也要向前看,「我們覺得學生、畢業生尊重承諾,尊重和團隊的溝通,其實都是重要的。」
石校長說:「我問自己,其實我要保護學生,保護他們的訴求,在這個過程之中,我有沒有同時都保護其他人?有沒有違反了教育精神或原則?因為我們愛人、保護學生,都有原則,就如剛剛關校長說過,若我們完全保護她們,去到最尾,是否又不需要守信用、守承諾?我們是很掙扎。很大的掙扎。其實我們本來是不需要有如此大的掙扎,如果同學不願意,她能早點提出,好像其他同學般,她能退出。張婉婷是夠片剪另一位學生進去,甚至只有五位都可以。但是很可惜,這個訴求無法逆轉。錯過了時機。」
「今時今日,我覺得很難過的是,錯過了時機。既然已錯過時機,事已至此,大家可否一起去想,大家是否也能夠做到互相都能夠接受的結果?很努力嘗試,如果最後都沒辦法,可能我們做抉擇時,就要思考究竟是要考慮大多數的好處,抑或是照顧一個學生而犧牲其他人?我很早期已和關校長說過,如果真的傷害了學生,那就不要放映。不放映也是一個選擇,但逐步逐步再看,不想放映的原因是什麼?是不夠保護?但是否不放映就能保護到她?我覺得這讓大家去思考。我自己前思後想,在一個如此困難的環境,真的很可惜。如果早點(提出),可能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本刊已就此事同時向導演要求回應,詳見後續報道。
文:丘瑞欣、盧乙彬
攝:黃家邦
(
《明周文化》2023年2月5日)
【給十九歲的我】英華女校重建 攝製十年紀錄片成焦點 張婉婷見證女生成長:一個神奇的經歷
由英華女學校發起,著名導演張婉婷歷時十年攝製,追蹤六位女生成長故事的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自去年首映起一直引起社會關注及熱議,上月更取得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1月28日,英華女學校舉行感恩及誓師大會,張婉婷聯同受訪女生、攝製隊重回母校,為紀錄片於2月2日正式全港公映宣傳。同日張婉婷接受本刊專訪,分享拍攝過程和感受。
從2012年開始拍攝一班中一女生,從她們十一、二歲,到今年二十三歲,正是見證她們由小朋友變成大人的轉變;看到她們長大成人,張婉婷十分感慨,「見到女仔咁靚,我好高興,真係愈長愈靚。」
《給十九歲的我》導演張婉婷(右三)、發起人計劃的時任校長李石玉如(中),以及片中女生馬燕茹(左一)、阿佘(左二)、Madam(左三)、阿雀 (右二)、Shirley(右一)。
《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意念是由時任校長李石玉如提出,半山羅便臣道校舍於2011年獲得原址重建的許可,需臨時遷往深水埗青山道校舍。按工程的進度估算,當年 (2011-2012 學年) 中一的新生,在羅便臣道校舍讀完一年後,便在深水埗臨時校舍繼續學業,並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年,重返新校舍,換言之該屆女生的六年中學生涯將經歷三代校舍;因此校方希望透過記錄校舍重建,拍攝這班女生的成長故事。
1968年於英華女學校畢業的張婉婷,對學校昔日資助她學習,一直懷有感恩之心,「因為我十五歲阿爸過身,校方俾晒所有獎學金、助學金我,免費午餐都俾我,這樣我先可以繼續讀書。」因此當石校長向她提出紀錄片拍攝計劃,她可說是義不容辭,「英華叫我做的事,我都沒拒絕過。」
好奇少女成長 珍惜「奉旨」拍攝機會
撇開校友身份,作為導演,她也認為此拍攝題材非常特別,而且機會難得,「你不是成日有機會睇住少女成長,你就算生了十幾個女,那些女都不會跟你傾咁多。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可以奉旨在學校裏周圍去訪問你所揀選的女仔,深入了解她們的性格和成長的過程。」
千禧一代的少女成長故事,勾起她滿滿的好奇心,「我自己成長時我就沒aware(為意),我都不知道、沒去分析自己成長,所以睇住她們,我覺得是一個幾神奇的經歷。果然真係好似《愛麗絲夢遊仙境》,一跌跌進洞裏面,你就見到很多奇形怪狀的物體那樣,即是好新鮮,我都沒想過她們會是這樣。」
說到挑選拍攝對象的準則,張婉婷說最重要是「她們要有獨立思想」,另一方面是家庭背景的多元性,如草根、中產、新移民及離婚家庭,「總之每個profile都是好有代表性。」
她憶述,最初拍攝時,攝製隊不知道該問她們什麼問題,也不認識對方,所以便決定「每個人都由頭到尾跟一日」的方法入手,「譬如一開始我來你屋企,由你起身開始,一直拍,拍到你上堂,完了學校去不同的補習班、鋼琴班、大提琴之類,返到屋企都已經七、八點,再看夜晚吃飯時有沒有阿爸阿媽陪伴,還是像阿佘那樣,自己一個吃晚飯,好孤清。」張婉婷說,「跟一日,但好多嘢你已經知道了──知道她和家庭的關係,學校裏跟同學的關係,上堂曳定唔曳,有沒有搞去長洲過夜的活動,放學要學幾多嘢⋯⋯一日就已經知道好多。」開學禮、散學禮、陸運會、水運會、音樂會等學校大型活動,鏡頭也從沒錯過,以紀錄她們校園生活點滴。
拍攝中途有學生退出 不強迫留低
中一剛開拍時,女生都對拍攝感到新奇、好玩,轉捩點是在中三時,「很多人都匿埋,不讓你拍。」女生阻擋鏡頭、講粗口以求中斷拍攝的片段,張婉婷最後也決定在紀錄片中呈現出來。面對一些女生對拍攝感到抗拒,不願繼續下去時,張婉婷強調:「說服是不行的,因為你點說服呢?『你拍啦!好有意義㗎!』難道講這些話?無用㗎,她們有自己的想法。」
「中間有些走了,有些不肯(拍),我們沒有所謂,我覺得最緊要就是唔好『監』她們做。一開始學校有同她們簽約,她們簽了約就應該繼續落去,footage應該是我們任意使用。但到中間她們大大吓,有一些人覺得自己私隱不想被人看到,那些人就走囉,她同我講就得。」
隨着拍攝到高中階段,她形容有些女生已經把她當成「死物」,彷彿不太記得攝影機的存在,「那時我覺得是拍攝的最高境界,因為當她不是太為意你在那裡,她繼續做返自己。」她認為既然她們願意繼續拍攝、接受訪問,就代表她們「已經想通了」、「接受了自己的故仔會被人睇到。」
究竟怎樣才能和女生建立到熟悉、信任的關係?張婉婷說,真誠做人,最重要是用心對待,「她覺得你不會abuse,不會亂用她的鏡頭,或者覺得她講的嘢是有意思的。」
不預設立場 爭取拍攝機會
在長期跟拍女生的過程中,攝製隊也出現過應否「介入」女生生活的掙扎,像「香港小姐」對於沒有家人陪她吃飯而難過不已,又擔憂自己患上癌症,於是攝製隊便陪她吃飯、帶她去看醫生;又如Madam英文成績欠佳,攝製隊便幫她補習英文。張婉婷這樣解釋:「現在的紀錄片的拍法和舊時《牆上的蒼蠅》差好遠,美國紀錄片導演Michael Moore直情是自己介入、有立場,我已經覺得我是無任何立場,但當見到她們在懸崖邊,你都會出手拉下佢,不可以讓她跌落去。」
張婉婷和幾個女生的關係也不錯,雖然有分組導演跟拍各個女孩,但阿聆和阿佘的部分,主要由她跟進。她主動提到,由她執導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大師微電影」的劇情短片之一《深藍》(2013年),邀請了阿聆和她的弟弟當主角,故事也以她兩姐弟的故事為藍本,此外,阿佘和阿雀亦有參與其中,飾演阿聆的同學。張婉婷稱讚阿聆、阿佘和阿雀「做戲都好叻」,「網上都可找到這部短片,這還是我第一次跟傳媒講。」她也承認,紀錄片中出現的一段飲品商業廣告片段是由她執導,那時她邀請了阿佘和其男朋友演出,造就片中的「戀愛訪問」場面。
六位主要受訪女生之外,Head Prefect Shirley也是紀錄片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女生。張婉婷表示,Shirley原不在拍攝名單上,因為她品學兼優、說話得體,給人太乖、面面俱圓的印象,令張覺得「冇咩故事」。直到後來阿佘「爆料」,說她和Shirley是best friend,Shirley作為Head Prefect,卻會「包庇」她,「我覺得這段友誼真的好震撼,一個咁品學兼優的Head Prefect,即全校最乖、老師選出來『第一名』,跟一個差不多是『尾名』、全部人杯葛,所以這段友誼好特別。」於是她便馬上在眾多片段中尋找Shirley,再把相關片段加進紀錄片。
張婉婷也特別難忘跟拍單車選手馬燕如出外比賽的經歷,當時馬要赴日本伊豆參加亞洲單車錦標賽,但攝製隊一直未能取得主辦單位的採訪批准,但因競賽畫面難得,在多年拍電影生涯中見慣風浪的張婉婷,膽粗粗就率領團隊「踩進」會場,信心十足的姿態令日本人信服其團隊的專業,任由他們在賽道近距離拍攝,全程沒有攔阻。期間因港隊隨團高層認出張婉婷,主動提供協助,甚至可安排李慧詩出場接受他們的訪問。張婉婷憶起這次經歷,泛起淺笑,神情自若輕鬆,顯出資深導演的架勢。
三十萬小時影像剪接血淚史
2019年新校舍落成,張婉婷、攝製隊和這些畢業兩年的女生一起參觀校舍,拍下她們對新校舍的感想,也訪問她們對於當時社會運動的看法,多年的拍攝正式告一段落,進入剪接階段。
張婉婷直言剪接比拍攝「辛苦十萬倍」,「(紀錄片)簡單過拍劇情片好多,但剪就死,死過劇情片好多,剛好相反。」由2012年至2019年,七年光景,三十萬小時影像,剪接團隊先剔出無關片段,其餘則打成逐字稿,從中選取合適片段。
經多個剪接版本,她最終決定以「編年史」方式說故事,按中一至中六順序呈現,並找出她們的共通點,像中一聚焦家庭背景、家人關係,從而帶出其成長背景,到中二她們開始追星、情竇初開,便定下「男神女神觀音兵」的主題。「 她們才是自己生命的導演。」張婉婷在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句旁白,她強調,作為紀錄片導演,不可以當劇情片一樣指揮拍攝對象的人生,「劇情片可以依自己,紀錄片完全是跟她們(受訪者),她們不是這樣,你沒理由搞到她們是另一個人,所以你看到影片,個個都好真實,就是這樣的人,無得將她們變成第二個人,而且會唔好睇,一定是做返她自己。」
希望電影不止英華人看
回想起校方最初向她提出拍攝記錄片的意念,並詢問她的意思,她表示:「如果我要花這麼多時間拍,首先就希望呢套戲(記錄片)不要只放在學校觀看,因為我要搵一個大的團隊去跟這些人六年,我都想拍一部『四正』的紀錄片,我們希望、發夢,有朝一日,這套戲不只是英華人睇,其他人也有興趣睇。」當時預計拍攝時間長達六年,太遙遠,更何況最終也未必能成事,張婉婷強調,一直視之為「一個dream」,努力向着目標前進,跟校方說,「不要浪費它,既然要拍這麼多年,如果拍得好、有人發行的話,那就可以去戲院放映。」
她坦言,紀錄片以普通女生為主角,而不是「絕代巨星」,就算電影公司聽她介紹後覺得「都幾得意」,也要「到時睇下個片」再決定。至剪接階段,張婉婷將部分初剪片段給發行公司「高先電影」創辦人曾麗芬考慮,對方看後覺得有意思的,就算不是「絕世鉅片」,這齣關於少女成長、社會變遷、十年變化的紀錄片,也是值得發行、應該幫忙的。
她指出,由於早有在校外放映的打算,因此在開拍前,校方已經跟學生及家長簽署合約,以示同意給予拍攝片段的任意使用及剪接權,「為了保障學校、(導演)團隊,也要保障這些女仔。」
片中人首看全片大感震驚
2021年12月1日,《給十九歲的我》全片首度面世,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校內籌款及放映活動,也是受訪女生首度觀看全片;22年8月21日《給十九歲的我》於第46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行世界首映,同年9月開始舉辧慈善放映專場、於高先電影上映優先場,並入圍倫敦東亞電影節、台北金馬影展等海外影展。
張婉婷說不論是受訪女生,還是石校長、周副校長,首次在大銀幕上觀看紀錄片全片,「個個都好震驚」,畢竟難以想像不到自己的樣子在大銀幕上的效果,也不記得了自己曾經說過的話。校方率先觀看全片後,「石校長話,『點解我講咁多嘢?』,我話『唔係好多啫』;小鳳(周副校長)又話,『我講用愛浸死佢哋,是不是好尷尬?你可不可以剪走它?』我話,『當然不可以啦,你講得最好是這句。」
至於受訪女生首度觀看全片的反應,「女仔睇完又震驚,於是大家就坐低,有小鳳、石校長、我們,看看大家有什麼感覺,就算我們以前簽了約,我都不想這些女仔不開心,套戲拿出來,我不想令到任何參與這套戲的人好似好苦。『因為我們簽咗約』,這是不行的,學校更加不想這樣發生,應該保護她們。」她表示該放映活動後,校方、女生討論了半年以上時間,嘗試梳理情感,了解有哪些「唔舒服」的地方,看看可以怎樣幫忙。
張婉婷說,當這些女生第一次看,「個個只係睇自己」、「好睇唔慣自己個樣」,也驚訝、擔心自己的說話內容敏感,看多幾次之後,才開始留意其他人,以更宏觀的心態觀影,「睇到整個picture,覺得自己只是兩個多小時的戲裏的一小撮,但就可以幫到一套戲,可以成就到這套戲,給很多人很多啟示。」她明白,要接受這些畫面放在大銀幕上給眾多觀眾看到,「要過到自己個關先得」,對於有女生想通、接受之後,她很感動,覺得她們「大個咗」,也很generous(慷慨)。
張舉Madam為例,起初看到自己從前滿懷理想當警察、最終無奈放棄,她感到十分尷尬,到後來覺得,「俾人睇到都冇所謂」,是因為她希望能撫平跟她有相同經歷的人;又如由震驚到表示「唔緊要,我硬食」的阿佘,張認為「可能是她已經接受了自己的過去」,「這是很難得的,因為心靈夠堅強的人,才能接受一個『咁嘅我』給世上所有人睇。」
文:丘瑞欣
攝:黃家邦 (部分圖片由高先電影提供)
Profile:
香港著名導演張婉婷,1950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及心理學,後於英國Bristol大學進修戲劇及寫作,並獲美國紐約大學電影碩士學位。
張婉婷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活躍華語影壇,與羅啟銳組成「情侶檔」,合力編、導多齣經典作品,人稱「雌雄大導」。1984年,張婉婷首次執導,憑《非法移民》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1987年執導的《秋天的童話》獲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1989年的《八両金》獲金像獎五項提名,是為其「移民三部曲」。重要導演作品還包括《宋家皇朝》、《玻璃之城》,以及監製電影《歲月神偷》,獲第60屆柏林影展新世代競賽單元最佳影片水晶熊獎。
張婉婷是現任香港電影導演會會長、香港電影發展局副主席,及香港國際電影節副主席。
(
《明周文化》2023年2月3日)
【《給十九歲的我》倫理爭議】紀錄片女生質疑拍攝倫理 張婉婷就此致歉 與校方決定暫停公映
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自周四(2月2日)上映後爭議不斷,兩位女生透過本刊表達對拍攝倫理的質疑後,本刊昨日曾向張婉婷導演要求回應,當時她沒有表明會暫停公映。惟張婉婷今日(2月5日)下午出席謝票場期間親自宣布,已跟英華女學校校董會達成共識,決定由周一(2月6日,星期一)開始暫停公映,讓各方有時間釐清有關問題,對於作品近日引起外界激烈討論,張導就此致歉。
張婉婷昨晚(2月4日)接受本刊電話訪問,回應《給》片中女生反映拍攝過程不受尊重、反對公開放映等問題。
對於近日有女生反映,在拍攝過程中感到不被尊重,張婉婷說她不清楚具體情況,她回想拍攝以來並沒有不尊重學生,知道她們是小朋友,要小心、加倍注意她們的想法。「我真的好尊重她們,反而成日佢哋鬧我就真,也不只我,我有很多分組導演,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在囈(求)她們,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權威去逼她們講嘢,因為她們不想講就會走,走便就走開了。」張又指,每年都會在校內播放錄影片段剪輯,給受訪女生和全校師生知悉拍攝進度,而當時沒有得到負面回應。
不過,片中六位主角首次觀看《給》紀錄片全片,要到2021年12月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校內籌款及放映活動上。她知道女生們看畢,無不大受驚嚇。「我都拍過好多人,我知道第一次在大銀幕看到自己,個個都好驚嚇。」此後,校方和女生多次溝通,了解其感受、情況。就張婉婷所知及理解,「大部分(女生)都可以放低,因為第一次看會較驚,再看多幾次,就開始接受自己,以及不只是看到自己,會成套戲去看,發覺整體套戲每人只佔廿幾分鐘,如果可以放寬懷抱,去睇埋成套戲,我想她們個個都覺得是有意思、有意義的一個Project。除了有一個(女生),她就放不開。」
包場反應正面 公映決定經校董會通過
張婉婷曾多次詢問該女生因由,亦曾將片中有關她的內容列表給她,希望知道是哪一些具體內容令她不滿,看看可否抽走相關內容,但不獲該女生答覆、解釋,她一直堅持要求剪走她在片中所有內容,「咁唔得啦,因為她是好後期(才提出要求),其實她早點講我們就得。」她續說,由於已經用了三年時間才完成剪接,整體結構難以更改,最多只能在細節上可作改動,所以「無從剪佢出嚟。」
相距首次校內放映活動半年多之後,去年8月,《給》於香港國際電影節世界首映。此後的放映活動安排,張婉婷形容是「逐步來」,「起初一直做包場,給宗教團體、教育團體、學術團體去看,看反應如何。我所能看到的反應之中,個個都覺得啲女生好啊、勇敢啊、可愛啊,無一個人對啲女仔有什麼異議,這令學校好放心。」由於坊間評價正面,除包場放映外,去年年尾亦舉行多場優先放映。
以她所知,學校一開始是希望六位女生都答應才會公映。不過,即使有一位女生一直都沒有同意公映,放映活動亦持續進行。「到最後經過那麼多階段,試過多次包場,個個女生都覺得放映好有意義,她們從中也見到自己的珍貴片段,終於覺得我們應該放映,因為社會氣氛都覺得好多人想看這套戲的,這是經過仔細衡量的,知道反應都真的很正面,所以覺得這是適當時候公開上映。」今年2月2日,《給》正式全港公映,張婉婷指有關決定是經校董會通過,「校董會考慮各方面、衡量所有,因為她是一個人against所有女生,她們已經同意了,還有所有工作了十年的人,校內老師、同學和其他持分者,我記得他們最後用法、理、情這點去講這件事。」
欣慰沒有一個女生受批評 自覺已保護她們
由拍攝階段,到現已全港公映,有女生認為過程中校方對學生保護不足,張婉婷認這樣說法對學校很不公平,「他們(學校)幾時無保護過?她們隨時可以走,學校沒有『監』她們去做。就算在我們最艱難的時刻,無人睬我們,學校也只是說『你等啦』,『用愛浸死佢哋』,學校完全沒有格硬要她們拍,亦都隨時哪個人走,就可以即刻走⋯⋯誰不會保護她們,我們沒有人保護就真,作為團隊,好苦啊覺得。」
最後,被問到作為導演,在她看來,究竟是人重要還是作品重要,她回答:「還是人更重要。我好欣慰這個作品出來後,沒有一個女仔受任何人批評,令我覺得我這個作品是保護了這些女仔。如果有任何一個女仔,受任何一個人的批評,或者學校受任何一個人的批評,我都會覺得好難過。但在所有公開(放映)、或者包場、或者公眾反應,沒有說她們不好,或說學校不好,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拍這電影最欣慰的事。」
1月28日,在英華女學校舉行的感恩及誓師大會上,張婉婷聯同受訪女生、攝製隊等重回母校,為紀錄片於2月2日正式全港公映宣傳。
文:丘瑞欣
攝:黃家邦
(
《明周文化》2023年2月4日)
昨日立春,今日元宵
【明報專訊】《給十九歲的我》正式公映,我們邀約片中女生做訪問,跟記者聊聊拍攝前後和種種。現在她們是成年人了,二十三歲,回望這段非一般經歷,恩怨愛恨,有喜有悲。理解自己跟被他人理解都非易事。有人仍在消化,努力應對個人與周遭的矛盾衝突,將不忿轉化,譬如阿佘(其實是Britney);阿雀依舊樂天;Madam(同學也沒有這樣叫她)好不容易安撫了自己那些提心吊膽的情緒;還有香港小姐,離開了香港的這些年,她學懂愛自己,用另一眼光看從前的小孩。感謝她們從大銀幕上跳出來坦誠分享,讓觀眾有機會聽見她們的心聲,可以補白看電影時的不安與疑慮,對她們和所有在成長路上跌跌撞撞的學子和年輕人,送上祝福。
昨日立春,今日是代表農曆新年節慶結束的元宵日,也是中國情人節。事實上仍有人在堅持立春過新年才是正路,新界地區昨晨零星響起爆竹聲。昨日開始,今日結束,中間的辛酸有誰知?感覺有點詭異。有另一個說法:今宵是新年第一個月圓之夜,逛綵燈會食湯圓等都是正經事。月亮今晚也是份外明,想要洗滌什麼都好,趁今晚。
(本網刊出的文章及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編者話˙黎佩芬
編輯•王翠麗
二十三歲的回望 《給十九歲的我》 實是兩代人磨合、理解和共處的記錄
(受訪者提供、片段撮圖)
(曾憲宗攝、片段撮圖)
(曾憲宗攝、片段撮圖)
(受訪者提供、片段撮圖)
【明報專訊】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上周正式上畫公映,電影攝製耗時10年,本為記錄英華女校重建,後來變成記錄6位女生從中一到19歲的成長故事,觀眾跟着導演的視角,看2011年到2019年香港的變化,也窺見少女成長路上的跌撞與蛻變。今年少女已23歲,她們又怎麼看他人眼中自己的成長?
■阿佘:不知道原來電影的重點是我們
在預告片中,有個女生晚上回到家自己一個人吃飯,說不喜歡媽媽,又不屑地在導演訪問鏡頭前轉身走人,導演叫她做阿佘。阿佘或許是觀眾看畢電影後印象最深刻、亦最關心的一位女生,至少記者很想知道這個特立獨行的女生近况如何,跟同學和家人關係如何,會否介意電影將其私隱公諸於世。
阿佘現在正修讀香港大學護理系,今年畢業。她在2021年12月電影首度放映、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校內籌款時,跟觀眾一樣,第一次看這套紀錄片。「其實好震驚,太多回憶recall出來,而且好多拍攝我的鏡頭,都是一些我過去的傷口,所以第一下看的時候,是好震驚和很不開心,因為情緒再次湧現。」
電影中,阿佘可說是大眾眼中的「離經叛道」,對鏡頭說話有些「寸寸貢」,為了不被跟拍所以對收音咪講粗口,放學不是去補習班而是拍拖、食煙。「我自己知道我的行為是離經叛道,但我真的不太care」,阿佘說電影中亦真實呈現了她的模樣,她從小到大都很堅持要做自己。「我會好想嘗試很多事,即使好多人會說『你會撞板呀』、『咁樣會害咗自己呀』,好多這些忠告,但是我想試,我就一定要試。」她倔強,說話直接、有時不留情面,這種性格也令她跟同學關係一直不好。
拍攝至高中時,鏡頭一轉,初中原本意氣風發、精心打扮的阿佘整個人憔悴了,這是她被杯葛得最嚴重、最崩潰的一年。她申請休學,跟所有同學保持距離,學會沉默,「如果以前口沒遮攔的話,那我就要學識完全一粒字都不講,不會因為有情緒牽動,就好想將所有東西講出來」。上學只想讀書和保護自己,比以前低調了,不再硬碰硬,「有些說話其實你可以不講,或者你知道你說了對方都不會明白,不如慳番啖氣啦」。現在她只對明白自己的人,或在重要的事上直白。「好多道理或者世事,我可能細個已經知,但細個說出來就有種不認命的倔強,現在的我都倔強,但會覺得無必要用好多心機,去testify這件事可不可以被改變。」
這是她對待《給十九歲的我》的態度,其實她對電影的內容、安排也有不滿。電影首次放映時,她和其他同學都沒有看過原片,這些年來團隊也沒有告知她電影何時會剪輯、有成品、如何放映。中一開拍時,計劃原本是想記錄校舍變遷、同學在3個校舍的校園生活,「現在無如期搬回校舍,我不知道原來電影的重點是我們,而且你覺得這套電影是代表英華,我都沒有想過導演會將很多不好的片段都放出來,所以都沒有想像過,無心理準備」。大銀幕把自己過去有關家庭關係、同學關係的傷口直接呈現在她眼前,她感到難受,也向導演和校方提出過不滿,但當時電影已經通過電檢,她們也曾簽同意書授權導演使用片段,她覺得自己無法阻止電影公映。「不妥協也只是嘥時間,所以妥協之後,處理好自己的心態更加重要、實際。」
不着眼負面影響 角色帶出信息
她自己消化電影會將自己傷口、私隱曝光的不安,「其實我不覺得我過去有什麼做得不對,或者我好後悔想改過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對得住自己就ok,不需要理別人點講」。她嘗試為電影賦予一個意義,不着眼於電影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再出席電影的映後談、誓師大會。「我的角色想表達的信息是,忠於自己,不要擔心其他人點睇你、點批評你,你也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她也想以自己的成長故事提醒大人要尊重年輕人,不要自以為是,「希望做家長或者做長輩的,會聽到小朋友的心聲,聆聽多啲,尊重多啲,先有尊重,才期望有溝通」。
阿佘說同學和老師其實多稱呼她做Britney。
■Madam:一個屬於我的個人歷史
Madam也不叫Madam,其實同學叫她做Karen。現在也可以稱呼她為Miss Law,因為她畢業後成為中學老師,教授地理和歷史,是升旗隊負責老師。電影正準備首次放映時,她正值大學四年級,剛好準備應徵老師職位,她極擔心電影放映後自己會被罵、會影響自己找工作,因為中學時的她對鏡頭說過自己想當警察。
Madam其實小六的時候已經立志做警察,因為想幫人。回想為什麼年紀小小就有如此宏大理想,她說可能是屋企影響。有次她跟同學鬧翻,那個同學遇上麻煩,她沒有幫忙,回家還幸災樂禍地跟家人分享,「我屋企人第一句是『你唔好咁樣啦,幫得就幫吖嘛』,『你理得佢好定壞,幫得就幫』」。她覺得,社會上好像什麼都關警察事,報失、捉賊、車禍、殺人放火也是警察處理,「我覺得很適合我去做,因為我都好想令個世界變好啲」。「你諗吓你返工已經返得好辛苦,臨收工嗰吓仲要畀人偷銀包,嗰個幸福感就會跌。」
她形容自己目標清晰,是會向着標竿直跑的人,電影拍攝了中學的她為了上大學、考督察,初中開始不用家人督促就會自己讀書。電影沒有拍攝她考進中文大學後的生活,但她依然沒有閒下來。大學生通常都把上課時間表編排到一兩天內把課全上完,其他日子就去玩、做兼職,她就排成周一至五都上天地堂,中間的空餘時間去健身室或運動場做運動,因為考警察要考體能。中大一年級要上體育課,通常學生都搶着報羽毛球、瑜伽等休閒體育項目,對要跑圈、做引體上升的體能鍛煉科避之則吉,她就專挑夏天上體能鍛煉,「因為我估計,未來無論是警察入班還是真的工作,你不可挑天氣,淋住雨、暴曬都要去」。她還報名做中大情緒紓緩和預防自殺熱線義工,一方面是想幫人,另外想訓練自己面對高壓環境,「因為有時突然一個電話埋嚟就跟你說他要自殺,然後你就會好慌張,我覺得這同時都是一個訓練」。大學實習她申請到警察公共關係科實習,協助辦少年警訊訓練營。
但2019年後,她放棄了這個志願,因為怕自己若真的堅持做警察,會連累家人。她也對警察這個理想感到迷惘,「這個職業有好人也有壞人,每個職業都是」。她未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想做警察,「有時也會想,唔通我未來就是做那班做得不好的人做的事?」老師是她的第二選擇,但她發現做老師不如當年實習般快樂。
電影快要放映時,她擔心得把自己社交媒體上,有關是英華、中大畢業的個人資訊全刪掉,怕被人網絡搜尋到自己,故意不看任何有關電影的評論。不過電影首次放映後,大多數評論都是正面,加上導演和校方的開導,她漸漸不介意電影對外放映。反正都播了第一場,評論也不全是負面,「那不如直接出街啦,唔爭在」。
電影也逼她直視自己對做不做警察的迷惘,告訴自己要有心理準備,一定會因為自己講過想做警察而被罵、聽到難聽的說話,學會不再在意別人的意見。「我無理由聽晒佢講,別人說不可以做這件事,但問題是,人生是我的。」她以前很想做到面面俱圓,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跟同學意見不合是自己問題,「但根本不能經常都符合晒全世界的期望」。
她性格直接,所以跟head prefect不和直說,導演問她如何看阿佘被杯葛時,她直說不同意杯葛阿佘的同學,2014年雨傘運動時也直說自己持反對立場。第一次看電影時她介意過這些片段,但最後也接受電影中過去的自己,「我覺得這是一個屬於我的個人歷史,就算導演刪剪了,這件事也已經發生了,人們常說錯話後收回自己的言論,我成日都覺得不會收得番,你講咗就係講咗」。她決定考警察,想做一個幫得就幫、對事不對人,不會帶有色眼鏡去看人的警察。
■香港小姐:看到愛哭的自己 今日識得愛自己
當年想做香港小姐的Katie現在身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在Ernst & Young做會計師。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說:「我細個都唔知點解會說上選港姐,如果我現在看以前的自己,我不覺得當年的自己有幾靚,還講得出我要選港姐,現在我肯定不會面皮這麼厚。」
「現在肯定不會面皮這麼厚」
香港小姐也是6名女生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個,父母離異,中二時媽媽一人到美國發展,只能把她暫託給親戚照顧,在最敏感的青春期,雙親都不在身旁。鏡頭拍着香港小姐的時候,好像大多數時間她都在哭。「我覺得以前的自己,脾氣比較差,諗嘢好鍾意諗歪一邊,好鍾意鑽牛角尖」,尤其在家庭關係上鑽牛角尖,「例如我去朋友家,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在身邊,你肯定會比較,小時候會覺得點解別人有但你無,還要兩個都無。」她曾跟鏡頭哭說暫住姨丈家的委屈,現在回看,香港小姐說其實是自己小時候誤解了,「有時如果發生一些事,我就覺得全世界只有我自己最慘,或者覺得自己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而不會看到全面。」
中三暑假後,香港小姐飛到美國跟媽媽團聚,在電影後半段甚少出現。觀眾或以為香港小姐自此就找回家庭溫暖、幸福快樂,但不然。「去了美國之後,我媽媽跟另外一個Uncle一起,Uncle有自己的小朋友,媽咪跟他又生了一個。」
重見媽媽,但媽媽不再只屬她
她找回媽媽,但媽媽不再只屬於她一個,「以前媽媽會將100%的愛給我,但她已經結了婚,有自己的小朋友,可能到你手的愛只剩下25%,心入面的得失會好重。」再加上要重新適應美國的校園生活,她入讀的高中一個亞洲人也沒有,同學全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鄰居,她很難融入他們的圈子,完全沒有傾訴對象。「天天都是pizza或者hamburger,完全食唔慣,我可能會帶家裏的飯去飯堂食,同學看到就會覺得你食緊好奇怪的物體,用好異樣的眼光望你。所以那段時間我自己拿着飯盒,偷偷去一個完全沒有人的地方食我的lunch,一整年的lunch都在那個地方度過。」她住的地方娛樂不多,高中生活就是每天放學後在家裏開的店打工。
沒有當年的事,不會有今日的我
於是她學會將生活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不再計較媽媽給予她幾多愛,不再因為家庭自怨自艾,而是將時間、心思專注在學業。「我當時就好清楚明白自己想去大城市發展,所以盡最大的努力,考去好的學校,再找一份喜歡的工作,盡最大努力去脫離令自己不開心的東西。」後來她考入University of Minnesota商科,以GPA 3.8的成績畢業。她說以前想做香港小姐的那個女生,跟現在的她很不一樣,無論是樣子、性格、興趣也截然不同,「我覺得人十幾年肯定會變,你以前可能說過一些說話,都不是經過你的大腦,或者現在重看自己說的東西,可能也不理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不是只有你自己一個是最慘,但最重要是向前望,清楚自己的目標,「外界看可能覺得我的故事真的比較慘,但如果沒有當年發生的事情,我都不會有今日的我,而今日的我會識得點樣去愛自己,和好好愛真的愛我的人。」
文˙朱琳琳
…………………………………………………………………
■阿雀:看到爸爸疼惜 憶起去世同學
在英華女學校門口,一眼就認出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六位主角之一的阿雀(倫凱頤)。二十三歲的阿雀,確實與鏡頭下圓滾滾的形象不同,瘦了,拔高了,淺啡長髮垂捲,但隱形眼鏡下那雙大大精靈眼睛,還是一樣。
問忽然變成半個公眾人物的她,沒有壓力嗎?她說,自己外表變化很大,沒人認得就無所謂啦,而且她留意到,很多觀眾像線上養多了個女兒一樣,很擔心這六個女仔後續如何,「所以,接受媒體訪問,想釋除大家的疑慮,也讓大家追看的戲有個結局」。片內金句「hea是一種生活態度」被人津津回味,她用力強調:「好多人問阿雀現在是否在返一份好hea的工,我可以好肯定地說,不是!」
拍攝之初
由校友張婉婷執導,《給十九歲的我》以六個中一女學生的生命故事,密密串連起學校由2011年半山羅便臣道的舊校舍,遷至2012年深水埗青山道的臨時校舍,再在2019年搬回原址新校舍的整修歷程。這不是張婉婷第一次與母校合作:2005年為蕭覺真校長製作紀念DVD,2010年又攝下校園大翻修前的《英華兒女的故事》,2011年開拍第三部曲《給十九歲的我》似乎順理成章──受時任校長石玉如邀請,加上校方出資,就答應了。
轉到學生視點,當年十來歲的她們又是如何理解「拍紀錄片」這回事?如片名所言,阿雀回憶,最開初同級五十多人被要求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後來即獲挑選,見導演面試:「答了很多問題。隔了段日子,學校發來一張通告,說你將會參與拍攝。」通告的簽名人理應是家長,但阿雀多年來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簽:「我媽說,她知道我何時去運動會、補課沒有意義,上學的人是我,要記住這些事的人是我,因此,只要我簽完告知她一聲可以了。」願意上鏡的原因,很單純:「通告通常有選擇的,而那時我和父母都想着一定要同意──讀書又不叻,被退學就麻煩了,學校叫到拍就拍啦。」
倫理爭議
那個簽名,或使阿雀比其他人多了份自覺責任,但對一個小女生而言,貼身拍攝仍是件麻煩事。記錄與被記錄的張力,在「學生日」第一次正式拍攝跑樓梯畫面時已充分呈現:「對學校和攝製隊來說,那天不用上課,是空了出來的回校假日。可是對中一學生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日子,無端端被佔用全日來拍攝,已很生氣,還要我不知為何被推到最前方——肥人做運動好辛苦,不用提跑上樓梯。我有個好朋友在最底層,說每次喊完cut,其實都沒怎樣動過,只有我在上面跑到死!導演說『笑吓啦』,我當下真的沒好氣,『跑得咁辛苦,你想我點笑?』」
全級去迪士尼卻一直被跟拍而「玩得不夠盡興」、其他人為避鏡頭不走近她身邊、同學向她抱怨早上不能在被攝的課室「光明正大交流功課」
……在最想融入群體的年紀被迫當個不平凡的校園明星,這種嫌麻煩甚至生氣的時刻在阿雀回憶的中學時光裏無數無數。和片中其他主角一樣,她最抗拒拍攝的日子在中二、中三,印象最深刻是被誤會「偷走」:「那天拍攝延遲,校內又不准用手提電話,於是走去門口,打算用一元打電話,向在地鐵站等自己的阿媽交代。怎料攝製隊看到我拿背囊就嚷,『你點可以偷走?咁樣唔啱、唔得㗎』,然後我遲到,又被阿媽炮轟罵我
……要走一早走了啦,好委屈。」
然而,不是外界所想那麼被動、無力,這群女生運轉的小小世界自有一套應對大人的方法。譬如,攝製隊千叮萬囑,別關上戴夾在衣衫的錄音咪,但她們左摸右摸,自動學懂「熄咪」:「去廁所的聲音沒理由被別人聽到吧,好奇怪。或者有時朋友之間想說悄悄話,不想被人聽到,都會關咪。」而她們不滿的聲音亦有人聆聽。阿雀記得一開始有位較專業的跟拍者,理所當然地假設學生乖乖配合,態度也比較兇惡;當她們向導演集體投訴後,隔天那人真的不見了,訪問團隊亦換上現在所見的一班業餘英華師姊「師奶兵團」。
橫越數十年的老少輩,說溝通沒有代溝、雙方沒有斷線崩潰的時刻,必然是假的。然而,兩者之間的誠摯信任,透過時間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由三十幾人汰選至後期的十幾人,多年來,被拍攝群中不乏退出的學生。阿雀為什麼願意留下來?她回想,中四時參演音樂劇Nightingale飾「肥雀」一角,是信任開始建立的轉捩點:「那時付出了很多心血去背台詞、登台練習,拍攝隊也一直隨我踩台、on show,慢慢覺得被關注不是那麼壞的事,至少,最後不論成果如何,都有條底片替我記下這份珍貴經驗。」她不忙調侃:「有時她們的問題都幾搞笑。例如,導演問我在音樂劇扮『阿雀』辛不辛苦──大佬,衫又重,妝又厚,台詞那麼長,根本明知故問。」經常各說各話卻又相互信任的微妙互動,構成這跨代關係的基石。正如「阿雀」其實是導演親暱喚她的花名,同齡朋友一般不會這樣稱呼她。《給十九歲的我》與其說是少女成長史,或者更是兩代人磨合、理解、共處的紀錄。
「總之佢哋問咩,我咪答咩囉。」阿雀如此笑笑總結。面對坊間不少論者質疑紀錄片的倫理道德,她說,自己沒權利改變任何人對這部戲的詮釋和解讀,「但老實講,如果彼此間沒有信任,整條片不可能出到街。」
珍貴片段
《給十九歲的我》在街外人眼裏,不過是一次觀影經驗,但在不同首映、公映場合一看再看,尷尬散去後的阿雀每次重看紀錄片,都會發現一些新意義。當中,與父親的相處片段尤為重要:「我與阿爸的年齡差是爺孫的程度。從紀錄片中一些好細節的位置,會見到他其實好疼錫我,只是用較粗漢的方式表達。以前覺得他駕電單車送出送入好惹人注目,不太情願,現在知道是一種照顧;又如深水埗的下雨天,阿爸突然一把抓起我,當下嫌他手濕黏黏、大叫鬆手,看到第三次,才發現原來前方有個水漥。」
相比隨時間模糊變改的記憶,影像是此曾在的實證。捕捉父母子女間的細微之愛以外,《給十九歲的我》亦無意間牽扯至人生人死的存在足印。阿雀憶及一位去年離世的同班同學,那人沒參與拍攝,只因為學號排在她前方,不經意被一同框進鏡頭。「她不和我特別親近,但派考試卷、派文憑試成績單、畢業禮等場合,都站在我旁邊。很記得片內某幕考試,她疾筆書寫,我在玩手指,那時還不用戴口罩,她的樣子清清楚楚在眼前──當刻衝擊好大,沒想過會在班相外重遇一個活生生的她。忽然就勾起腦內一些記憶碎片:我對她炫耀自己考通識全級第一好叻,話不多的她輕輕回我的傻話,『係啊係啊,好叻啊你』;放榜日我好緊張地告訴她,『死啦,好緊張好驚』
……是極其珍貴的回憶。」
以為十年時間總會徹底改變一個人,但某些性格、特質的原點扎在體內,似乎會一直依沿發展。回望過去,二十三歲的阿雀覺得內在變化不大,「我還是那個『阿雀』」。訪問後,我看着她,跟在攝影師背後擺着手一跳一跳,像隻雀仔,不禁覺得確是這樣。
文•吳騫桐
圖•曾憲宗、受訪者提供、片段撮圖
編輯•王翠麗
(《明報》2023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