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歌》月刊
許定銘
在中國現文學史上有三種叫《新詩歌》的雜誌:其一是中國詩歌會在一九三三年出的旬日會刊;其次是延安新詩歌會在一九四O年出的會刊;第三種是現在大家見到的,一九四七年二月,由春草社在上海創辦的《新詩歌》。
《新詩歌》是本十六開,僅十八頁的月刊,其特點在「反映人民的呼聲」及「以方言入詩」,編輯三人組,由薛汕負責搜集民謠、李凌編歌曲、沙鷗則專注於新詩,這是本真真正正集「詩」與「歌」於一身的雜誌,經常在這兒發表作品的有:臧克家、蘇金傘、臧雲遠、覃子豪、柳倩、王亞平、穆木天……,都是當時滬上的名詩人。
我藏的這本《新詩歌》是一至五期的合訂本,五期的封面均有不同的顏色,但用的都是刃鋒這幅本刻,充分反映出「勞動群眾力量的偉大」。書後有〈本刊啟事〉,說「本刊經費及編輯方針,一向獨立,不受任何經發處所左右……自第六期起改為叢刊,稍後繼續出版,並由春草社負發行之責」。
原來《新詩歌》出版以來一直受到政府的壓力,說雜誌背後另有政治目的,經常借故騷擾並查禁,叢刊也僅出了《黑色的詛咒》一期,最終難逃停刊的命運,幾個編輯也要逃到香港避難去!
《新詩歌叢書》
許定銘
一九四八年初,薛汕和沙鷗到了香港,計劃復刊《新詩歌》。在黨的華南分局文委領導下,創辦了「新詩歌社」,加入了大量當時活躍的詩人:戈陽、黄雨、丹木、江華、海蒙、犁青……等,並在是年二月出版了《新詩歌》叢刊第七輯《晴天一聲雷》,以後又出了《被迫害的行列》、《血染紅了華山》、《顆顆送給子弟兵》和《今年唔同去年》等輯。
除了《新詩歌》叢刊,他們還出過一套《新詩歌叢書》。關於這套叢書,《中國近現代叢書目錄》(上海圖書館編,一九七九)只記錄了黃雨的《殘夜集》和海蒙的《激變》;薛汕發表於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新文學史料》中的回憶文章〈四十年代的《新詩歌》〉中,多提了戈陽的《血仇》、沙鷗的《燒村》、童晴嵐的《狼》、薛汕輯的《嶺南謠》和江華譯的《囉嗦家》;我手邊還有力揚的《射虎者》和沙鷗的《百醜圖》是他未提及的,此至,我手上的《新詩歌叢書》共九種,其實也未必收齊。
這套《新詩歌叢書》有同一構圖的封面,比三十六開略小(10.5x15.5cm),全部都是五十頁左右的小冊子,出版於一九四八年八月至十二月間,每種僅印五百冊,非常罕見!
沙鷗的兩本小書
許定銘
原名王世達的詩人沙鷗(1922~1994),是四川重慶人,一九四二年入中華大學,學的是化學,但他早在一九四O年已發表詩作了。他在抗戰後期加入「春草社」,與晏明合編《詩叢》,後到上海與薛汕合編《新詩歌》。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編《新詩歌》叢刊時,還編了一套《新詩歌叢書》,此中收編了他自己的《燒村》和《百醜圖》。
《燒村》全書只有四十八頁,是一首寫於一九四七年的長詩,詩分四章,叙述了八年抗戰中,四川農村中農民的苦難面影。「他們有的破產了,把僅餘的土地也落進了大戶的手中,有的成了赤貧,從佃農變成了貧農……」他給我們看的是苦難的四川鄉野。
《百醜圖》有六十四頁,是本收有十一首詩的詩集。沙鷗一直擅寫農民的苦困,提倡詩要大眾化,要能以方言入詩,而甚少寫「政治諷刺詩」;但,在香港生活的一年來,沙鷗與老家的農村失去了聯繫,在海隅的大都市裡,能清楚的看到「蔣朝那些破船上的海盜們,那種不停的爭吵,那種使人哭笑不得的醜態」,使他不得不作出大膽和新奇的嘗試,以諷刺的筆法,把當權派的百醜圖繪出來!
黃雨的《殘夜集》
許定銘
原名黃遺的廣東澄海詩人黃雨(1916~1991),常用的筆名還有丁東父。他一九四七年來港,在香島中學及中業學院教書,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並從事詩創作及方言文學研究,與新詩歌社詩友沙鷗、薛汕等交往,並出版了《新詩歌叢書》之一的《殘夜集》(香港新詩歌社,一九四八),此詩集僅印五百冊,相當罕見。
《殘夜集》只有五十頁,收七首新詩,除了〈歌白毛女〉外,其餘六首詩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村景〉、〈老婦〉、〈示眾〉、〈將軍〉和〈鄉書〉寫戰後小鄉鎮的殘景,這裡有戰後的斷垣殘壁,有期待當軍的兒子歸來的母親,有被誣蔑賣國的校長,有戰敗卻欺壓善良村民的將軍……戰爭勝利了,但人民得到的卻是亂後的哀痛,再哀痛!另一組的〈蕭頓球場的黃昏〉和〈給露宿者〉,則以香港為背景,寫大城市中貧富懸殊的差距,暴露社會的陰暗面。
黃雨在〈後記〉中說,他戰後回到闊別八年的家鄉,「看到了新貴們的貪婪橫暴,和人民在繼續受難」,感到無比的憤恨,但礙於形勢,只好鬱在心裡。直到一九四七年流浪到香港,才能以詩篇向社會發出控訴。《殘夜集》中的幾首詩,是新中國建立前的殘夜景象。
童晴嵐和他的《狼》
許定銘
童晴嵐(1909~1979)是中國詩歌會中較少人提到的詩人,抗戰時候,他以詩集《南中國的歌》(詩歌出版社,一九三七) 享譽詩壇。蒲風在該書的序中,讚揚他能明察我們的時代,指出南中國的危機,並無時不在鼓吹及怒吼抗日,掀起怒濤。抗日時期,「童晴嵐」是和《南中國的歌》及「愛國熱情」這些語詞連成一起,極受推崇的。可惜,《南中國的歌》和他的另一本詩集《中華轟炸機》(厦門詩歌會,一九三八)都相當罕見,我只有大家現時見到的《狼》(香港新詩歌社,一九四八)。
《狼》是首三百五十行的長篇叙事詩,寫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先在香港新詩歌叢刊《被迫害的行列》中刊出,然後出單行本。全詩以六章叙說善良的貧農黃五哥,看不過羅鄉長强迫村民林伯鈞去當兵,並把他的妻子收作偏房;又强行把官鹽抬價以搜刮村民的財產,便聯合村民反抗。羅鄉長便把黃五哥拉去築路,把他打傷,丟給餓狼……。
《狼》暴露了善良的村民在暴政下生活的苦痛,無辜斷送生命是極平常的事。官員和「狼」其實是同類的生物,而慘絕人寰的悲劇,無時無刻不在鄉間上演。沙鷗在讚揚《狼》時,說此詩「隱藏在樸素的詩句中的血淚,是如此深深地感動人,這感動將使我們更憎惡橫蠻」、腐敗的政權!
許定銘
在中國現文學史上有三種叫《新詩歌》的雜誌:其一是中國詩歌會在一九三三年出的旬日會刊;其次是延安新詩歌會在一九四O年出的會刊;第三種是現在大家見到的,一九四七年二月,由春草社在上海創辦的《新詩歌》。
《新詩歌》是本十六開,僅十八頁的月刊,其特點在「反映人民的呼聲」及「以方言入詩」,編輯三人組,由薛汕負責搜集民謠、李凌編歌曲、沙鷗則專注於新詩,這是本真真正正集「詩」與「歌」於一身的雜誌,經常在這兒發表作品的有:臧克家、蘇金傘、臧雲遠、覃子豪、柳倩、王亞平、穆木天……,都是當時滬上的名詩人。
我藏的這本《新詩歌》是一至五期的合訂本,五期的封面均有不同的顏色,但用的都是刃鋒這幅本刻,充分反映出「勞動群眾力量的偉大」。書後有〈本刊啟事〉,說「本刊經費及編輯方針,一向獨立,不受任何經發處所左右……自第六期起改為叢刊,稍後繼續出版,並由春草社負發行之責」。
原來《新詩歌》出版以來一直受到政府的壓力,說雜誌背後另有政治目的,經常借故騷擾並查禁,叢刊也僅出了《黑色的詛咒》一期,最終難逃停刊的命運,幾個編輯也要逃到香港避難去!
《新詩歌叢書》
許定銘
一九四八年初,薛汕和沙鷗到了香港,計劃復刊《新詩歌》。在黨的華南分局文委領導下,創辦了「新詩歌社」,加入了大量當時活躍的詩人:戈陽、黄雨、丹木、江華、海蒙、犁青……等,並在是年二月出版了《新詩歌》叢刊第七輯《晴天一聲雷》,以後又出了《被迫害的行列》、《血染紅了華山》、《顆顆送給子弟兵》和《今年唔同去年》等輯。
除了《新詩歌》叢刊,他們還出過一套《新詩歌叢書》。關於這套叢書,《中國近現代叢書目錄》(上海圖書館編,一九七九)只記錄了黃雨的《殘夜集》和海蒙的《激變》;薛汕發表於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新文學史料》中的回憶文章〈四十年代的《新詩歌》〉中,多提了戈陽的《血仇》、沙鷗的《燒村》、童晴嵐的《狼》、薛汕輯的《嶺南謠》和江華譯的《囉嗦家》;我手邊還有力揚的《射虎者》和沙鷗的《百醜圖》是他未提及的,此至,我手上的《新詩歌叢書》共九種,其實也未必收齊。
這套《新詩歌叢書》有同一構圖的封面,比三十六開略小(10.5x15.5cm),全部都是五十頁左右的小冊子,出版於一九四八年八月至十二月間,每種僅印五百冊,非常罕見!
沙鷗的兩本小書
許定銘
原名王世達的詩人沙鷗(1922~1994),是四川重慶人,一九四二年入中華大學,學的是化學,但他早在一九四O年已發表詩作了。他在抗戰後期加入「春草社」,與晏明合編《詩叢》,後到上海與薛汕合編《新詩歌》。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編《新詩歌》叢刊時,還編了一套《新詩歌叢書》,此中收編了他自己的《燒村》和《百醜圖》。
《燒村》全書只有四十八頁,是一首寫於一九四七年的長詩,詩分四章,叙述了八年抗戰中,四川農村中農民的苦難面影。「他們有的破產了,把僅餘的土地也落進了大戶的手中,有的成了赤貧,從佃農變成了貧農……」他給我們看的是苦難的四川鄉野。
《百醜圖》有六十四頁,是本收有十一首詩的詩集。沙鷗一直擅寫農民的苦困,提倡詩要大眾化,要能以方言入詩,而甚少寫「政治諷刺詩」;但,在香港生活的一年來,沙鷗與老家的農村失去了聯繫,在海隅的大都市裡,能清楚的看到「蔣朝那些破船上的海盜們,那種不停的爭吵,那種使人哭笑不得的醜態」,使他不得不作出大膽和新奇的嘗試,以諷刺的筆法,把當權派的百醜圖繪出來!
黃雨的《殘夜集》
許定銘
原名黃遺的廣東澄海詩人黃雨(1916~1991),常用的筆名還有丁東父。他一九四七年來港,在香島中學及中業學院教書,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並從事詩創作及方言文學研究,與新詩歌社詩友沙鷗、薛汕等交往,並出版了《新詩歌叢書》之一的《殘夜集》(香港新詩歌社,一九四八),此詩集僅印五百冊,相當罕見。
《殘夜集》只有五十頁,收七首新詩,除了〈歌白毛女〉外,其餘六首詩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村景〉、〈老婦〉、〈示眾〉、〈將軍〉和〈鄉書〉寫戰後小鄉鎮的殘景,這裡有戰後的斷垣殘壁,有期待當軍的兒子歸來的母親,有被誣蔑賣國的校長,有戰敗卻欺壓善良村民的將軍……戰爭勝利了,但人民得到的卻是亂後的哀痛,再哀痛!另一組的〈蕭頓球場的黃昏〉和〈給露宿者〉,則以香港為背景,寫大城市中貧富懸殊的差距,暴露社會的陰暗面。
黃雨在〈後記〉中說,他戰後回到闊別八年的家鄉,「看到了新貴們的貪婪橫暴,和人民在繼續受難」,感到無比的憤恨,但礙於形勢,只好鬱在心裡。直到一九四七年流浪到香港,才能以詩篇向社會發出控訴。《殘夜集》中的幾首詩,是新中國建立前的殘夜景象。
童晴嵐和他的《狼》
許定銘
童晴嵐(1909~1979)是中國詩歌會中較少人提到的詩人,抗戰時候,他以詩集《南中國的歌》(詩歌出版社,一九三七) 享譽詩壇。蒲風在該書的序中,讚揚他能明察我們的時代,指出南中國的危機,並無時不在鼓吹及怒吼抗日,掀起怒濤。抗日時期,「童晴嵐」是和《南中國的歌》及「愛國熱情」這些語詞連成一起,極受推崇的。可惜,《南中國的歌》和他的另一本詩集《中華轟炸機》(厦門詩歌會,一九三八)都相當罕見,我只有大家現時見到的《狼》(香港新詩歌社,一九四八)。
《狼》是首三百五十行的長篇叙事詩,寫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先在香港新詩歌叢刊《被迫害的行列》中刊出,然後出單行本。全詩以六章叙說善良的貧農黃五哥,看不過羅鄉長强迫村民林伯鈞去當兵,並把他的妻子收作偏房;又强行把官鹽抬價以搜刮村民的財產,便聯合村民反抗。羅鄉長便把黃五哥拉去築路,把他打傷,丟給餓狼……。
《狼》暴露了善良的村民在暴政下生活的苦痛,無辜斷送生命是極平常的事。官員和「狼」其實是同類的生物,而慘絕人寰的悲劇,無時無刻不在鄉間上演。沙鷗在讚揚《狼》時,說此詩「隱藏在樸素的詩句中的血淚,是如此深深地感動人,這感動將使我們更憎惡橫蠻」、腐敗的政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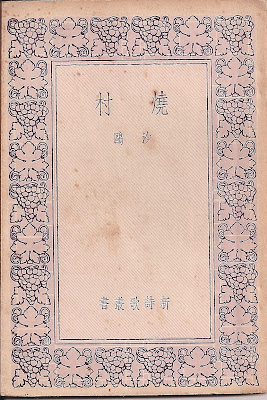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