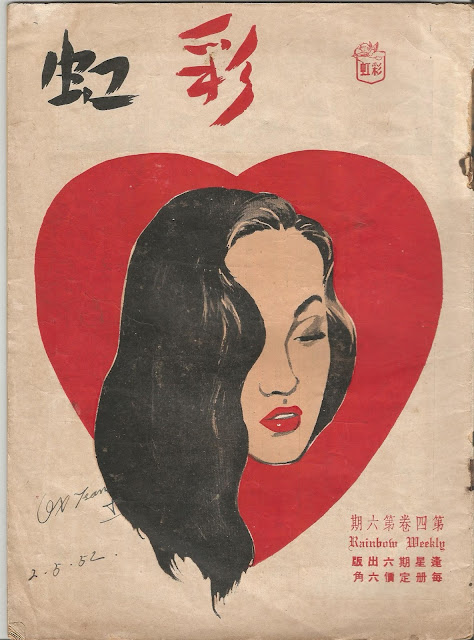東方文學叢刊
一九六O年代,香港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屬下新設的東方文學社,出過一批十餘種的《東方文學叢刊》。這批書在純創作方面有:郭良蕙《戀愛的悲喜劇》、梁園的《鬼湖的故事》、艾鳴的《淚湖》、趙之誠的《喜從天降》、童真的《黛綠的季節》、蔡文甫的《解凍的時候》、王晶心 等的《古樹春藤》、王潔心等的《美蓮姐姐》……。這套書有個特殊的現象:作者多為外地的作家,如郭良蕙、童真等來自台灣,梁園則是南洋作家。郭良蕙、童真、蔡文甫等當年已薄有名氣,應該可以贏得本地讀者,但,梁園、趙之誠和艾鳴等的書,銷量大概不會很好。
蔡文甫寫過十多本小說,後來還辦了「九歌出版社」,專門出版文學書,是著名的文化人。一九六O年代初,他常為香港的《文壇》、《中國學生周報》等報刊寫小說,《東方文學叢刊》中的《解凍的時候》(香港東方文學社,一九六三),是他第一部小說集,收《生命之歌》、《寂寞的世界》、《草帽、襪子與黃瓜》、《圓舞曲》……等十四個短篇。蔡文甫的小說着重心理描寫,刻劃細膩以外,還很着意把主人翁的幻想訴諸筆墨,使現實與想像的畫面,在文字上交織成片段,突顯了他和她內心的矛盾。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的《小飯店裏的故事》、《放鳥記》和《解凍的時候》,是集中最出色的幾篇。
柳存仁的《人物譚》
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的柳存仁(1917~2009)博士,晚年定居澳洲,是馳譽世界的學者,專研中國舊小說及道教。其實他讀中學時已開始創作,經常投稿到《論語》和《人間世》,抗戰時期已出過散文集《西星集》 (上海宇宙風社,1940)、《懷鄉記》(署名柳雨生,上海太平書局,1944) 和小說《撻妻記》(署名柳雨生,上海雜誌社,1944)。
柳存仁一九四六年到香港,曾任教於皇仁書院和羅富國師範學校,居港多年,寫過不少劇本,也出了不少書,其中我比較喜歡的,是如今大家見到的《人物譚》(香港大公書局,1952)。
顧名思義,《人物譚》是本寫「人」的書。寫人物,當然要寫自己有興趣,知道較深入的人,才能駕輕就熟發揮自如,而讀者也可以憑此知道寫作人肚內的墨水及其研讀方向。柳存仁的《人物譚》中收文三十多篇,所談人物有全人皆知的耶穌、釋迦,近代作家魯迅、章太炎、蕭伯納,古代的宰相、太監,藝術家楊小樓……均入其筆下。柳存仁在序中說他是研究歷史的,因此,在談人物時,少不免也談了制度、風俗,旁及零星的考證,這可見作者學問之博,也正是其功力的所在。
正版《人物譚》已面世六十年,難得一見,不過,此書一九七O年代有翻印本,圖書館中或仍可見,不宜錯失!
素葉叢書
三十多年來一直是「素葉出版社」主幹的許廸鏘,在談及創社過程的《在流行與不流行之間抉擇》(見《素葉文學》五十九期)中說,他們辦出版社的目的是出版香港作者的書。在這許多年中,他們出版過六十多種叢書和《素葉文學》期刊。在香港這個商業主導的國際大都會,「文學」一向是極小的「微塵」,素葉仝人默默耕耘幾十年,不接受任何資助,自掏腰包,自發的奉獻,不得不提提他們:西西、張灼祥、何福仁、許廸鏘、鍾玲玲、辛其氏 ……這群「文學發燒友」。
「素葉」是先有《文學叢書》才有《素葉文學》的。第一輯出於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只出西西的《我城》、鍾玲玲《我的燦爛》、何福仁《龍的訪問》和淮遠的《鸚鵡韆鞦》四種,小說、詩和散文都有;後來才有鄭樹森《奥菲爾斯的變奏》、李維陵的《隔閡集》、戴天的《渡渡這種鳥》、馬博良《焚琴的浪子》、董橋《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這些叢書如今大多絕版,有些在拍賣會上還被搶到數百元以上。早期這批叢書的封面設計大多出自蔡浩泉手筆,「蔡頭」騎鶴西去十年有多,如此可愛的構圖已成絕響。
《我城》是叢書的第一種,出版時我在灣仔開書店,西西間中來,簽名贈我,珍藏至今。幾十年未見,近況可好?
陳炳藻的小說
一九七O年代初,在威斯康辛大學得文學博士,一直在美國各大學任教的陳炳藻,是香港的留學生。雖然他以英文著述《電腦紅學:論紅樓夢作者》(香港三聯,一九八六)一書廣為人知,其實他早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一九六四年已開始小說創作,並出版過短篇小說集《投影》(香港山邊社,一九八三) 和《就那麼一點黯紅》(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
《投影》是他的處女集,收《膿》、《狗種》、《拒》、《相煎》、《面譜以外》……等十二個短篇,差不多全是一九六O年代發表於香港的少作。不過,水平已相當高,此中寫於一九六五年的《潮的旋律》,在《中國學生周報》的徵文比賽中得過獎;寫流落香港白俄生活的《籬邊的音樂》,被收入與西西、亦舒、欒復(蔡炎培)等人合著的《新人小說選》(香港友聯,一九六八)中;而他自己最喜歡的,則是寫他大哥的《投影》。
我手上有份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芷蘭季刊》第三期,是我們「芷蘭文藝社」的社刊,陳炳藻以筆名「丙早」,在此發表了五千字的短篇《裏外流》,寫大學剛畢業的孟嘉麗思想流的矛盾:留在大學裏當助教好呢?還是到她嚮往的西方留學好?這是陳炳藻早期創作的成功作品之一,描寫細膩以外,矛盾與抉擇之間的忐忑不安尤其恰到好處,何以不選進《投影》裏?
黃蒙田的回憶
黄蒙田(1916~1997)抗戰勝利後即長期居港,繪畫、寫評論、小說,編文藝雜誌……,他一生寫了三十九本書,最後的兩本:《黃蒙田散文回憶篇》和《黃蒙田序跋集》都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鑪峰文叢」,前者出版於一九九六,是他一手一腳整理的。在後記中,他還哀痛地說「整理這本小書是一次痛苦的經歷,由於這些文章接觸到的朋友都不在了」;想不到的是,一年後當他編好《黃蒙田序跋集》要出版時,連後記也來不及寫就撒手西去,還要羅琅代筆及校對出書,人生何其無奈!
黃蒙田在香港文化界活動半世紀,《黃蒙田散文回憶篇》中二十多篇回憶性質文章所涉及的,像葉靈鳳、新波、侶倫、鷗外鷗、余所亞、夏果、李凡夫……,都是本地重要的文化工作者,由和他們交往多年的黃蒙田親述,資料尤其翔實可靠,特別是《小記葉苗秀》,更是唯一談苗秀的文章。
苗秀原是侶倫、望雲、平可那一代的文人,後來改變風格,替報紙副刊寫雜文謀生,自認為是稿匠或寫稿佬,每日早上工作,用幾小時寫了幾千字後,即到高陞茶樓與朋友擺龍門陣。他用花菴、藏園、吉金、鷗閣、澹生……十多個筆名寫稿,主要從日文雜誌選材重寫,葉靈鳳年代的《星島‧星座》一天會登他幾篇。活躍於五六十年代的苗秀,是神話式的寫字人。